捆绑 10000字
文章摘要:高三作文10000字:怎么写好捆绑10000字作文?经年以后,你可知晓,那老旧的路灯以及灰黄灯光下凝固的点滴,早已被时光拆除,不留痕迹。与你的邂逅恍如昨日。那时我从酒吧出来,背着吉他,拖着整夜奏唱的疲惫。你坐在路灯下轻声啜泣,那缕缕悲伤和着凌晨四点时刻清凉被我敏感的耳膜捕捉,我在想,是怎样一个女子,哭出我吉他奏不出的悲凉。以下是叶惠萍写的《捆绑》范文;
好捆绑作文10000字概况
- 作者:叶惠萍
- 班级:高中高三
- 字数:10000字作文
- 体裁:
- 段落:分127段叙写
- 更新:2024年03月09日 08时18分
经年以后,你可知晓,那老旧的路灯以及灰黄灯光下凝固的点滴,早已被时光拆除,不留痕迹。
与你的邂逅恍如昨日。
那时我从酒吧出来,背着吉他,拖着整夜奏唱的疲惫。你坐在路灯下轻声啜泣,那缕缕悲伤和着凌晨四点时刻清凉被我敏感的耳膜捕捉,我在想,是怎样一个女子,哭出我吉他奏不出的悲凉。
我找到了你,在最边角一个摇摇欲坠的路灯下,它在苟延残喘地发出些微弱的灯光。你看见我,我亦看见你眸中闪烁的泪光,一如江南的水。你见我没有恶意,或者你不在乎我的存在,便继续将头埋入手臂。我在你身旁大概一米远的地方坐下,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便取出吉他,用我已歌唱了一晚干涩的喉咙为你吟唱。是一首外国的歌,叫Maybe in the hand,原唱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人未成名,歌未被传唱,却早早地离开人世,带走了一身绝世才华。
我唱得很认真,没有察觉你何时停止哭泣,我也不清楚我为何歌唱,甚至至今也不知道,是为那早夭的生命,还是为那伤情的眼泪。
其实我唱了很久,似乎是两三遍,这是许久以后你告诉我的。你说你并未听清我的吟唱,只是反复的旋律,和逐渐熟悉的歌词。你说在我唱到第一遍的高潮时,你就停止了流泪,因为我比你更投入,你的眼泪或许虚伪甚至矫情,但我的吉他却早已被我的真融化。
然后是无关伤痛的浅聊,我知道对于你这样单纯的女子无非是失恋所带来的痛楚,而你说你在我的嗓音里认识了其它更触动你的东西,很隐密,却很深刻。
你的女友肯定很幸福吧,你说。不知道,我淡淡地回答,拨动吉他继续唱起来,音乐会让人有种连毒品都难以匹敌的瘾。你很不解,然后细细揣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并不相爱。我停下来转过头去对你微笑,说,你猜得很对,我和她,并不相爱,只是单纯的陪伴和互相之间一些浅浅的依赖。
然后我就一直唱到了天亮,你则在我旁边不停地诉说着刚和你分手的男友的一切,也不管我是否在听。你细数着他一切的不好,从头至尾让我逐渐厌烦,但我还是未抱怨,只轻轻挑拨吉他浅唱,控制着音量不以免打扰你。
天亮的以后我们分别,我说,你只记得他的不好,那他的好呢?你的表情再次临暗,嚅嚅着,他的好我都记着,他的很多不好其实我都能容忍,只是他的最大的不好我没有说,现在告诉你,他不相信我。我沉默,然后点头说我懂了。
记得很久以后你对我说,两个在一起,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其它一切需要以它为基础,如果失去了信任,便什么也没有了。
我叫蓝,你呢?你离开数步以后忽然回头问我。哦,我一边收好吉他,一边抬头,我,叫鱼。
你曾说我是一条不会游泳的鱼,要是死,也是被水淹死。我说你叫蓝却不喜欢蓝色,这又是为何。而那时我们在一起的日子,离初次见面和如今,都有很长一段日子了吧。
如果说初次见面是偶遇,那么第二次开始,我们就在经历着种种命中注定。或许冥冥中的定数真的难以改变,我们只能默默接受生活赐予的一切而无法抱怨,因为那只是徒劳。
你来酒吧买醉,我在前台唱歌,从阴暗的混沌里直接透过肮脏的幕幕看到了你的眼睛,依旧是泪,依旧流淌着江南的水。你看到我的时候似乎很惊异,不过只是瞬间。你继续埋进酒瓶堆里,我继续拨动吉他歌唱,只是那一次,我唱的是摇滚。
下班的时候我来到你身边,拍拍你,你看了我一眼,便默默地跟来。我依旧在那昏黄的路灯下为你吟唱,只是一曲未终,你便睡去,我想,你是醉了。
我把你带回我的住所,一个租来的小阁楼,窗户对着一棵很大的槐树,花开的季节,地板上会铺满清香。
第二天你在我的歌声中醒来,从房间出来看见我,然后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把卫生间指给你,说你去梳洗,该轮我睡了。你问我唱了多久,我只是摇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我对时间没有概念,我只知道白天和黑夜,没有分没有秒。
我醒的时候你还在,翻看着我的书桌上的旅游杂志,惊奇地问我是不是也喜欢西藏,我笑着点头。我说我喜欢墨脱。你说你的他本来也要带你去西藏的,不过他同别的女孩去了。
我问你为何不走,你说今天是星期天没有课,况且这里很温暖,你无家可归,回学校也无聊,便留下了。
我点点头,然后去准备饭菜,你却说现在是三点,午饭时间已经过了,再忍忍吃晚饭吧。我说我从不计较时间,饿了就吃。你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没有什么正当的职业,晚上在酒吧唱歌,白天写字,写一些没有多少人爱看的严肃文学,勉强过活,没有什么牵绊。经年以后,你可知晓,那老旧的路灯以及灰黄灯光下凝固的点滴,早已被时光拆除,不留痕迹。与你的邂逅恍如昨日。
那时我从酒吧出来,背着吉他,拖着整夜奏唱的疲惫。你坐在路灯下轻声啜泣,那缕缕悲伤和着凌晨四点时刻清凉被我敏感的耳膜捕捉,我在想,是怎样一个女子,哭出我吉他奏不出的悲凉。
我找到了你,在最边角一个摇摇欲坠的路灯下,它在苟延残喘地发出些微弱的灯光。你看见我,我亦看见你眸中闪烁的泪光,一如江南的水。你见我没有恶意,或者你不在乎我的存在,便继续将头埋入手臂。我在你身旁大概一米远的地方坐下,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便取出吉他,用我已歌唱了一晚干涩的喉咙为你吟唱。是一首外国的歌,叫Maybe in the hand,原唱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人未成名,歌未被传唱,却早早地离开人世,带走了一身绝世才华。
我唱得很认真,没有察觉你何时停止哭泣,我也不清楚我为何歌唱,甚至至今也不知道,是为那早夭的生命,还是为那伤情的眼泪。
其实我唱了很久,似乎是两三遍,这是许久以后你告诉我的。你说你并未听清我的吟唱,只是反复的旋律,和逐渐熟悉的歌词。你说在我唱到第一遍的高潮时,你就停止了流泪,因为我比你更投入,你的眼泪或许虚伪甚至矫情,但我的吉他却早已被我的真融化。
然后是无关伤痛的浅聊,我知道对于你这样单纯的女子无非是失恋所带来的痛楚,而你说你在我的嗓音里认识了其它更触动你的东西,很隐密,却很深刻。
你的女友肯定很幸福吧,你说。不知道,我淡淡地回答,拨动吉他继续唱起来,音乐会让人有种连毒品都难以匹敌的瘾。你很不解,然后细细揣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并不相爱。我停下来转过头去对你微笑,说,你猜得很对,我和她,并不相爱,只是单纯的陪伴和互相之间一些浅浅的依赖。
然后我就一直唱到了天亮,你则在我旁边不停地诉说着刚和你分手的男友的一切,也不管我是否在听。你细数着他一切的不好,从头至尾让我逐渐厌烦,但我还是未抱怨,只轻轻挑拨吉他浅唱,控制着音量不以免打扰你。
天亮的以后我们分别,我说,你只记得他的不好,那他的好呢?你的表情再次临暗,嚅嚅着,他的好我都记着,他的很多不好其实我都能容忍,只是他的最大的不好我没有说,现在告诉你,他不相信我。我沉默,然后点头说我懂了。
记得很久以后你对我说,两个在一起,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其它一切需要以它为基础,如果失去了信任,便什么也没有了。
我叫蓝,你呢?你离开数步以后忽然回头问我。哦,我一边收好吉他,一边抬头,我,叫鱼。
你曾说我是一条不会游泳的鱼,要是死,也是被水淹死。我说你叫蓝却不喜欢蓝色,这又是为何。而那时我们在一起的日子,离初次见面和如今,都有很长一段日子了吧。
如果说初次见面是偶遇,那么第二次开始,我们就在经历着种种命中注定。或许冥冥中的定数真的难以改变,我们只能默默接受生活赐予的一切而无法抱怨,因为那只是徒劳。
你来酒吧买醉,我在前台唱歌,从阴暗的混沌里直接透过肮脏的幕幕看到了你的眼睛,依旧是泪,依旧流淌着江南的水。你看到我的时候似乎很惊异,不过只是瞬间。你继续埋进酒瓶堆里,我继续拨动吉他歌唱,只是那一次,我唱的是摇滚。
下班的时候我来到你身边,拍拍你,你看了我一眼,便默默地跟来。我依旧在那昏黄的路灯下为你吟唱,只是一曲未终,你便睡去,我想,你是醉了。
我把你带回我的住所,一个租来的小阁楼,窗户对着一棵很大的槐树,花开的季节,地板上会铺满清香。
第二天你在我的歌声中醒来,从房间出来看见我,然后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把卫生间指给你,说你去梳洗,该轮我睡了。你问我唱了多久,我只是摇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我对时间没有概念,我只知道白天和黑夜,没有分没有秒。
我醒的时候你还在,翻看着我的书桌上的旅游杂志,惊奇地问我是不是也喜欢西藏,我笑着点头。我说我喜欢墨脱。你说你的他本来也要带你去西藏的,不过他同别的女孩去了。
我问你为何不走,你说今天是星期天没有课,况且这里很温暖,你无家可归,回学校也无聊,便留下了。
我点点头,然后去准备饭菜,你却说现在是三点,午饭时间已经过了,再忍忍吃晚饭吧。我说我从不计较时间,饿了就吃。你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没有什么正当的职业,晚上在酒吧唱歌,白天写字,写一些没有多少人爱看的严肃文学,勉强过活,没有什么牵绊。经年以后,你可知晓,那老旧的路灯以及灰黄灯光下凝固的点滴,早已被时光拆除,不留痕迹。与你的邂逅恍如昨日。
那时我从酒吧出来,背着吉他,拖着整夜奏唱的疲惫。你坐在路灯下轻声啜泣,那缕缕悲伤和着凌晨四点时刻清凉被我敏感的耳膜捕捉,我在想,是怎样一个女子,哭出我吉他奏不出的悲凉。
我找到了你,在最边角一个摇摇欲坠的路灯下,它在苟延残喘地发出些微弱的灯光。你看见我,我亦看见你眸中闪烁的泪光,一如江南的水。你见我没有恶意,或者你不在乎我的存在,便继续将头埋入手臂。我在你身旁大概一米远的地方坐下,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便取出吉他,用我已歌唱了一晚干涩的喉咙为你吟唱。是一首外国的歌,叫Maybe in the hand,原唱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人未成名,歌未被传唱,却早早地离开人世,带走了一身绝世才华。
我唱得很认真,没有察觉你何时停止哭泣,我也不清楚我为何歌唱,甚至至今也不知道,是为那早夭的生命,还是为那伤情的眼泪。
其实我唱了很久,似乎是两三遍,这是许久以后你告诉我的。你说你并未听清我的吟唱,只是反复的旋律,和逐渐熟悉的歌词。你说在我唱到第一遍的高潮时,你就停止了流泪,因为我比你更投入,你的眼泪或许虚伪甚至矫情,但我的吉他却早已被我的真融化。
然后是无关伤痛的浅聊,我知道对于你这样单纯的女子无非是失恋所带来的痛楚,而你说你在我的嗓音里认识了其它更触动你的东西,很隐密,却很深刻。
你的女友肯定很幸福吧,你说。不知道,我淡淡地回答,拨动吉他继续唱起来,音乐会让人有种连毒品都难以匹敌的瘾。你很不解,然后细细揣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并不相爱。我停下来转过头去对你微笑,说,你猜得很对,我和她,并不相爱,只是单纯的陪伴和互相之间一些浅浅的依赖。
然后我就一直唱到了天亮,你则在我旁边不停地诉说着刚和你分手的男友的一切,也不管我是否在听。你细数着他一切的不好,从头至尾让我逐渐厌烦,但我还是未抱怨,只轻轻挑拨吉他浅唱,控制着音量不以免打扰你。
天亮的以后我们分别,我说,你只记得他的不好,那他的好呢?你的表情再次临暗,嚅嚅着,他的好我都记着,他的很多不好其实我都能容忍,只是他的最大的不好我没有说,现在告诉你,他不相信我。我沉默,然后点头说我懂了。
记得很久以后你对我说,两个在一起,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其它一切需要以它为基础,如果失去了信任,便什么也没有了。
我叫蓝,你呢?你离开数步以后忽然回头问我。哦,我一边收好吉他,一边抬头,我,叫鱼。
你曾说我是一条不会游泳的鱼,要是死,也是被水淹死。我说你叫蓝却不喜欢蓝色,这又是为何。而那时我们在一起的日子,离初次见面和如今,都有很长一段日子了吧。
如果说初次见面是偶遇,那么第二次开始,我们就在经历着种种命中注定。或许冥冥中的定数真的难以改变,我们只能默默接受生活赐予的一切而无法抱怨,因为那只是徒劳。
你来酒吧买醉,我在前台唱歌,从阴暗的混沌里直接透过肮脏的幕幕看到了你的眼睛,依旧是泪,依旧流淌着江南的水。你看到我的时候似乎很惊异,不过只是瞬间。你继续埋进酒瓶堆里,我继续拨动吉他歌唱,只是那一次,我唱的是摇滚。
下班的时候我来到你身边,拍拍你,你看了我一眼,便默默地跟来。我依旧在那昏黄的路灯下为你吟唱,只是一曲未终,你便睡去,我想,你是醉了。
我把你带回我的住所,一个租来的小阁楼,窗户对着一棵很大的槐树,花开的季节,地板上会铺满清香。
第二天你在我的歌声中醒来,从房间出来看见我,然后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把卫生间指给你,说你去梳洗,该轮我睡了。你问我唱了多久,我只是摇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我对时间没有概念,我只知道白天和黑夜,没有分没有秒。
我醒的时候你还在,翻看着我的书桌上的旅游杂志,惊奇地问我是不是也喜欢西藏,我笑着点头。我说我喜欢墨脱。你说你的他本来也要带你去西藏的,不过他同别的女孩去了。
我问你为何不走,你说今天是星期天没有课,况且这里很温暖,你无家可归,回学校也无聊,便留下了。
我点点头,然后去准备饭菜,你却说现在是三点,午饭时间已经过了,再忍忍吃晚饭吧。我说我从不计较时间,饿了就吃。你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没有什么正当的职业,晚上在酒吧唱歌,白天写字,写一些没有多少人爱看的严肃文学,勉强过活,没有什么牵绊。经年以后,你可知晓,那老旧的路灯以及灰黄灯光下凝固的点滴,早已被时光拆除,不留痕迹。与你的邂逅恍如昨日。
那时我从酒吧出来,背着吉他,拖着整夜奏唱的疲惫。你坐在路灯下轻声啜泣,那缕缕悲伤和着凌晨四点时刻清凉被我敏感的耳膜捕捉,我在想,是怎样一个女子,哭出我吉他奏不出的悲凉。
我找到了你,在最边角一个摇摇欲坠的路灯下,它在苟延残喘地发出些微弱的灯光。你看见我,我亦看见你眸中闪烁的泪光,一如江南的水。你见我没有恶意,或者你不在乎我的存在,便继续将头埋入手臂。我在你身旁大概一米远的地方坐下,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便取出吉他,用我已歌唱了一晚干涩的喉咙为你吟唱。是一首外国的歌,叫Maybe in the hand,原唱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人未成名,歌未被传唱,却早早地离开人世,带走了一身绝世才华。
我唱得很认真,没有察觉你何时停止哭泣,我也不清楚我为何歌唱,甚至至今也不知道,是为那早夭的生命,还是为那伤情的眼泪。
其实我唱了很久,似乎是两三遍,这是许久以后你告诉我的。你说你并未听清我的吟唱,只是反复的旋律,和逐渐熟悉的歌词。你说在我唱到第一遍的高潮时,你就停止了流泪,因为我比你更投入,你的眼泪或许虚伪甚至矫情,但我的吉他却早已被我的真融化。
然后是无关伤痛的浅聊,我知道对于你这样单纯的女子无非是失恋所带来的痛楚,而你说你在我的嗓音里认识了其它更触动你的东西,很隐密,却很深刻。
你的女友肯定很幸福吧,你说。不知道,我淡淡地回答,拨动吉他继续唱起来,音乐会让人有种连毒品都难以匹敌的瘾。你很不解,然后细细揣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并不相爱。我停下来转过头去对你微笑,说,你猜得很对,我和她,并不相爱,只是单纯的陪伴和互相之间一些浅浅的依赖。
然后我就一直唱到了天亮,你则在我旁边不停地诉说着刚和你分手的男友的一切,也不管我是否在听。你细数着他一切的不好,从头至尾让我逐渐厌烦,但我还是未抱怨,只轻轻挑拨吉他浅唱,控制着音量不以免打扰你。
天亮的以后我们分别,我说,你只记得他的不好,那他的好呢?你的表情再次临暗,嚅嚅着,他的好我都记着,他的很多不好其实我都能容忍,只是他的最大的不好我没有说,现在告诉你,他不相信我。我沉默,然后点头说我懂了。
记得很久以后你对我说,两个在一起,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其它一切需要以它为基础,如果失去了信任,便什么也没有了。
我叫蓝,你呢?你离开数步以后忽然回头问我。哦,我一边收好吉他,一边抬头,我,叫鱼。
你曾说我是一条不会游泳的鱼,要是死,也是被水淹死。我说你叫蓝却不喜欢蓝色,这又是为何。而那时我们在一起的日子,离初次见面和如今,都有很长一段日子了吧。
如果说初次见面是偶遇,那么第二次开始,我们就在经历着种种命中注定。或许冥冥中的定数真的难以改变,我们只能默默接受生活赐予的一切而无法抱怨,因为那只是徒劳。
你来酒吧买醉,我在前台唱歌,从阴暗的混沌里直接透过肮脏的幕幕看到了你的眼睛,依旧是泪,依旧流淌着江南的水。你看到我的时候似乎很惊异,不过只是瞬间。你继续埋进酒瓶堆里,我继续拨动吉他歌唱,只是那一次,我唱的是摇滚。
下班的时候我来到你身边,拍拍你,你看了我一眼,便默默地跟来。我依旧在那昏黄的路灯下为你吟唱,只是一曲未终,你便睡去,我想,你是醉了。
我把你带回我的住所,一个租来的小阁楼,窗户对着一棵很大的槐树,花开的季节,地板上会铺满清香。
第二天你在我的歌声中醒来,从房间出来看见我,然后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把卫生间指给你,说你去梳洗,该轮我睡了。你问我唱了多久,我只是摇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我对时间没有概念,我只知道白天和黑夜,没有分没有秒。
我醒的时候你还在,翻看着我的书桌上的旅游杂志,惊奇地问我是不是也喜欢西藏,我笑着点头。我说我喜欢墨脱。你说你的他本来也要带你去西藏的,不过他同别的女孩去了。
我问你为何不走,你说今天是星期天没有课,况且这里很温暖,你无家可归,回学校也无聊,便留下了。
我点点头,然后去准备饭菜,你却说现在是三点,午饭时间已经过了,再忍忍吃晚饭吧。我说我从不计较时间,饿了就吃。你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没有什么正当的职业,晚上在酒吧唱歌,白天写字,写一些没有多少人爱看的严肃文学,勉强过活,没有什么牵绊。经年以后,你可知晓,那老旧的路灯以及灰黄灯光下凝固的点滴,早已被时光拆除,不留痕迹。与你的邂逅恍如昨日。
那时我从酒吧出来,背着吉他,拖着整夜奏唱的疲惫。你坐在路灯下轻声啜泣,那缕缕悲伤和着凌晨四点时刻清凉被我敏感的耳膜捕捉,我在想,是怎样一个女子,哭出我吉他奏不出的悲凉。
我找到了你,在最边角一个摇摇欲坠的路灯下,它在苟延残喘地发出些微弱的灯光。你看见我,我亦看见你眸中闪烁的泪光,一如江南的水。你见我没有恶意,或者你不在乎我的存在,便继续将头埋入手臂。我在你身旁大概一米远的地方坐下,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便取出吉他,用我已歌唱了一晚干涩的喉咙为你吟唱。是一首外国的歌,叫Maybe in the hand,原唱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人未成名,歌未被传唱,却早早地离开人世,带走了一身绝世才华。
我唱得很认真,没有察觉你何时停止哭泣,我也不清楚我为何歌唱,甚至至今也不知道,是为那早夭的生命,还是为那伤情的眼泪。
其实我唱了很久,似乎是两三遍,这是许久以后你告诉我的。你说你并未听清我的吟唱,只是反复的旋律,和逐渐熟悉的歌词。你说在我唱到第一遍的高潮时,你就停止了流泪,因为我比你更投入,你的眼泪或许虚伪甚至矫情,但我的吉他却早已被我的真融化。
然后是无关伤痛的浅聊,我知道对于你这样单纯的女子无非是失恋所带来的痛楚,而你说你在我的嗓音里认识了其它更触动你的东西,很隐密,却很深刻。
你的女友肯定很幸福吧,你说。不知道,我淡淡地回答,拨动吉他继续唱起来,音乐会让人有种连毒品都难以匹敌的瘾。你很不解,然后细细揣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并不相爱。我停下来转过头去对你微笑,说,你猜得很对,我和她,并不相爱,只是单纯的陪伴和互相之间一些浅浅的依赖。
然后我就一直唱到了天亮,你则在我旁边不停地诉说着刚和你分手的男友的一切,也不管我是否在听。你细数着他一切的不好,从头至尾让我逐渐厌烦,但我还是未抱怨,只轻轻挑拨吉他浅唱,控制着音量不以免打扰你。
天亮的以后我们分别,我说,你只记得他的不好,那他的好呢?你的表情再次临暗,嚅嚅着,他的好我都记着,他的很多不好其实我都能容忍,只是他的最大的不好我没有说,现在告诉你,他不相信我。我沉默,然后点头说我懂了。
记得很久以后你对我说,两个在一起,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其它一切需要以它为基础,如果失去了信任,便什么也没有了。
我叫蓝,你呢?你离开数步以后忽然回头问我。哦,我一边收好吉他,一边抬头,我,叫鱼。
你曾说我是一条不会游泳的鱼,要是死,也是被水淹死。我说你叫蓝却不喜欢蓝色,这又是为何。而那时我们在一起的日子,离初次见面和如今,都有很长一段日子了吧。
如果说初次见面是偶遇,那么第二次开始,我们就在经历着种种命中注定。或许冥冥中的定数真的难以改变,我们只能默默接受生活赐予的一切而无法抱怨,因为那只是徒劳。
你来酒吧买醉,我在前台唱歌,从阴暗的混沌里直接透过肮脏的幕幕看到了你的眼睛,依旧是泪,依旧流淌着江南的水。你看到我的时候似乎很惊异,不过只是瞬间。你继续埋进酒瓶堆里,我继续拨动吉他歌唱,只是那一次,我唱的是摇滚。
下班的时候我来到你身边,拍拍你,你看了我一眼,便默默地跟来。我依旧在那昏黄的路灯下为你吟唱,只是一曲未终,你便睡去,我想,你是醉了。
我把你带回我的住所,一个租来的小阁楼,窗户对着一棵很大的槐树,花开的季节,地板上会铺满清香。
第二天你在我的歌声中醒来,从房间出来看见我,然后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把卫生间指给你,说你去梳洗,该轮我睡了。你问我唱了多久,我只是摇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我对时间没有概念,我只知道白天和黑夜,没有分没有秒。
我醒的时候你还在,翻看着我的书桌上的旅游杂志,惊奇地问我是不是也喜欢西藏,我笑着点头。我说我喜欢墨脱。你说你的他本来也要带你去西藏的,不过他同别的女孩去了。
我问你为何不走,你说今天是星期天没有课,况且这里很温暖,你无家可归,回学校也无聊,便留下了。
我点点头,然后去准备饭菜,你却说现在是三点,午饭时间已经过了,再忍忍吃晚饭吧。我说我从不计较时间,饿了就吃。你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没有什么正当的职业,晚上在酒吧唱歌,白天写字,写一些没有多少人爱看的严肃文学,勉强过活,没有什么牵绊。经年以后,你可知晓,那老旧的路灯以及灰黄灯光下凝固的点滴,早已被时光拆除,不留痕迹。与你的邂逅恍如昨日。
那时我从酒吧出来,背着吉他,拖着整夜奏唱的疲惫。你坐在路灯下轻声啜泣,那缕缕悲伤和着凌晨四点时刻清凉被我敏感的耳膜捕捉,我在想,是怎样一个女子,哭出我吉他奏不出的悲凉。
我找到了你,在最边角一个摇摇欲坠的路灯下,它在苟延残喘地发出些微弱的灯光。你看见我,我亦看见你眸中闪烁的泪光,一如江南的水。你见我没有恶意,或者你不在乎我的存在,便继续将头埋入手臂。我在你身旁大概一米远的地方坐下,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便取出吉他,用我已歌唱了一晚干涩的喉咙为你吟唱。是一首外国的歌,叫Maybe in the hand,原唱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人未成名,歌未被传唱,却早早地离开人世,带走了一身绝世才华。
我唱得很认真,没有察觉你何时停止哭泣,我也不清楚我为何歌唱,甚至至今也不知道,是为那早夭的生命,还是为那伤情的眼泪。
其实我唱了很久,似乎是两三遍,这是许久以后你告诉我的。你说你并未听清我的吟唱,只是反复的旋律,和逐渐熟悉的歌词。你说在我唱到第一遍的高潮时,你就停止了流泪,因为我比你更投入,你的眼泪或许虚伪甚至矫情,但我的吉他却早已被我的真融化。
然后是无关伤痛的浅聊,我知道对于你这样单纯的女子无非是失恋所带来的痛楚,而你说你在我的嗓音里认识了其它更触动你的东西,很隐密,却很深刻。
你的女友肯定很幸福吧,你说。不知道,我淡淡地回答,拨动吉他继续唱起来,音乐会让人有种连毒品都难以匹敌的瘾。你很不解,然后细细揣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并不相爱。我停下来转过头去对你微笑,说,你猜得很对,我和她,并不相爱,只是单纯的陪伴和互相之间一些浅浅的依赖。
然后我就一直唱到了天亮,你则在我旁边不停地诉说着刚和你分手的男友的一切,也不管我是否在听。你细数着他一切的不好,从头至尾让我逐渐厌烦,但我还是未抱怨,只轻轻挑拨吉他浅唱,控制着音量不以免打扰你。
天亮的以后我们分别,我说,你只记得他的不好,那他的好呢?你的表情再次临暗,嚅嚅着,他的好我都记着,他的很多不好其实我都能容忍,只是他的最大的不好我没有说,现在告诉你,他不相信我。我沉默,然后点头说我懂了。
记得很久以后你对我说,两个在一起,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其它一切需要以它为基础,如果失去了信任,便什么也没有了。
我叫蓝,你呢?你离开数步以后忽然回头问我。哦,我一边收好吉他,一边抬头,我,叫鱼。
你曾说我是一条不会游泳的鱼,要是死,也是被水淹死。我说你叫蓝却不喜欢蓝色,这又是为何。而那时我们在一起的日子,离初次见面和如今,都有很长一段日子了吧。
如果说初次见面是偶遇,那么第二次开始,我们就在经历着种种命中注定。或许冥冥中的定数真的难以改变,我们只能默默接受生活赐予的一切而无法抱怨,因为那只是徒劳。
你来酒吧买醉,我在前台唱歌,从阴暗的混沌里直接透过肮脏的幕幕看到了你的眼睛,依旧是泪,依旧流淌着江南的水。你看到我的时候似乎很惊异,不过只是瞬间。你继续埋进酒瓶堆里,我继续拨动吉他歌唱,只是那一次,我唱的是摇滚。
下班的时候我来到你身边,拍拍你,你看了我一眼,便默默地跟来。我依旧在那昏黄的路灯下为你吟唱,只是一曲未终,你便睡去,我想,你是醉了。
我把你带回我的住所,一个租来的小阁楼,窗户对着一棵很大的槐树,花开的季节,地板上会铺满清香。
第二天你在我的歌声中醒来,从房间出来看见我,然后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把卫生间指给你,说你去梳洗,该轮我睡了。你问我唱了多久,我只是摇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我对时间没有概念,我只知道白天和黑夜,没有分没有秒。
我醒的时候你还在,翻看着我的书桌上的旅游杂志,惊奇地问我是不是也喜欢西藏,我笑着点头。我说我喜欢墨脱。你说你的他本来也要带你去西藏的,不过他同别的女孩去了。
我问你为何不走,你说今天是星期天没有课,况且这里很温暖,你无家可归,回学校也无聊,便留下了。
我点点头,然后去准备饭菜,你却说现在是三点,午饭时间已经过了,再忍忍吃晚饭吧。我说我从不计较时间,饿了就吃。你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没有什么正当的职业,晚上在酒吧唱歌,白天写字,写一些没有多少人爱看的严肃文学,勉强过活,没有什么牵绊。经年以后,你可知晓,那老旧的路灯以及灰黄灯光下凝固的点滴,早已被时光拆除,不留痕迹。与你的邂逅恍如昨日。
那时我从酒吧出来,背着吉他,拖着整夜奏唱的疲惫。你坐在路灯下轻声啜泣,那缕缕悲伤和着凌晨四点时刻清凉被我敏感的耳膜捕捉,我在想,是怎样一个女子,哭出我吉他奏不出的悲凉。
我找到了你,在最边角一个摇摇欲坠的路灯下,它在苟延残喘地发出些微弱的灯光。你看见我,我亦看见你眸中闪烁的泪光,一如江南的水。你见我没有恶意,或者你不在乎我的存在,便继续将头埋入手臂。我在你身旁大概一米远的地方坐下,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便取出吉他,用我已歌唱了一晚干涩的喉咙为你吟唱。是一首外国的歌,叫Maybe in the hand,原唱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人未成名,歌未被传唱,却早早地离开人世,带走了一身绝世才华。
我唱得很认真,没有察觉你何时停止哭泣,我也不清楚我为何歌唱,甚至至今也不知道,是为那早夭的生命,还是为那伤情的眼泪。
其实我唱了很久,似乎是两三遍,这是许久以后你告诉我的。你说你并未听清我的吟唱,只是反复的旋律,和逐渐熟悉的歌词。你说在我唱到第一遍的高潮时,你就停止了流泪,因为我比你更投入,你的眼泪或许虚伪甚至矫情,但我的吉他却早已被我的真融化。
然后是无关伤痛的浅聊,我知道对于你这样单纯的女子无非是失恋所带来的痛楚,而你说你在我的嗓音里认识了其它更触动你的东西,很隐密,却很深刻。
你的女友肯定很幸福吧,你说。不知道,我淡淡地回答,拨动吉他继续唱起来,音乐会让人有种连毒品都难以匹敌的瘾。你很不解,然后细细揣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并不相爱。我停下来转过头去对你微笑,说,你猜得很对,我和她,并不相爱,只是单纯的陪伴和互相之间一些浅浅的依赖。
然后我就一直唱到了天亮,你则在我旁边不停地诉说着刚和你分手的男友的一切,也不管我是否在听。你细数着他一切的不好,从头至尾让我逐渐厌烦,但我还是未抱怨,只轻轻挑拨吉他浅唱,控制着音量不以免打扰你。
天亮的以后我们分别,我说,你只记得他的不好,那他的好呢?你的表情再次临暗,嚅嚅着,他的好我都记着,他的很多不好其实我都能容忍,只是他的最大的不好我没有说,现在告诉你,他不相信我。我沉默,然后点头说我懂了。
记得很久以后你对我说,两个在一起,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其它一切需要以它为基础,如果失去了信任,便什么也没有了。
我叫蓝,你呢?你离开数步以后忽然回头问我。哦,我一边收好吉他,一边抬头,我,叫鱼。
你曾说我是一条不会游泳的鱼,要是死,也是被水淹死。我说你叫蓝却不喜欢蓝色,这又是为何。而那时我们在一起的日子,离初次见面和如今,都有很长一段日子了吧。
如果说初次见面是偶遇,那么第二次开始,我们就在经历着种种命中注定。或许冥冥中的定数真的难以改变,我们只能默默接受生活赐予的一切而无法抱怨,因为那只是徒劳。
你来酒吧买醉,我在前台唱歌,从阴暗的混沌里直接透过肮脏的幕幕看到了你的眼睛,依旧是泪,依旧流淌着江南的水。你看到我的时候似乎很惊异,不过只是瞬间。你继续埋进酒瓶堆里,我继续拨动吉他歌唱,只是那一次,我唱的是摇滚。
下班的时候我来到你身边,拍拍你,你看了我一眼,便默默地跟来。我依旧在那昏黄的路灯下为你吟唱,只是一曲未终,你便睡去,我想,你是醉了。
我把你带回我的住所,一个租来的小阁楼,窗户对着一棵很大的槐树,花开的季节,地板上会铺满清香。
第二天你在我的歌声中醒来,从房间出来看见我,然后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把卫生间指给你,说你去梳洗,该轮我睡了。你问我唱了多久,我只是摇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我对时间没有概念,我只知道白天和黑夜,没有分没有秒。
我醒的时候你还在,翻看着我的书桌上的旅游杂志,惊奇地问我是不是也喜欢西藏,我笑着点头。我说我喜欢墨脱。你说你的他本来也要带你去西藏的,不过他同别的女孩去了。
我问你为何不走,你说今天是星期天没有课,况且这里很温暖,你无家可归,回学校也无聊,便留下了。
我点点头,然后去准备饭菜,你却说现在是三点,午饭时间已经过了,再忍忍吃晚饭吧。我说我从不计较时间,饿了就吃。你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没有什么正当的职业,晚上在酒吧唱歌,白天写字,写一些没有多少人爱看的严肃文学,勉强过活,没有什么牵绊。

好文章,赞一下
332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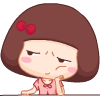
很一般,需努力
432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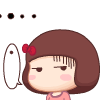
太差劲,踩一下
21人
- 上一篇:牵挂作文1000字
- 下一篇:帮李敏走出困境作文55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