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到荼縻,花事了 10000字
文章摘要:高三作文10000字:怎么写好开到荼縻,花事了10000字作文?我一直不知道荼縻竟然是一种小花,清雅的白色,淡然的芬芳,像一个女子心中的爱情,静寂的,内敛的,在内心寂寞地盛开--<林花谢了>妃子靠墙根蹲着,黑黑亮亮的眼睛淹没在这片儿地域的乌烟障气和墨镜的黑色投影里。以下是蔡海峰写的《开到荼縻,花事了》范文;
好开到荼縻,花事了作文10000字概况
- 作者:蔡海峰
- 班级:高中高三
- 字数:10000字作文
- 体裁:
- 段落:分127段叙写
- 更新:2022年03月19日 04时40分
我一直不知道荼縻竟然是一种小花,清雅的白色,淡然的芬芳,像一个女子心中的爱情,静寂的,内敛的,在内心寂寞地盛开--<林花谢了>
妃子靠墙根蹲着,黑黑亮亮的眼睛淹没在这片儿地域的乌烟障气和墨镜的黑色投影里。说黑黑亮亮也不太对,昨天整宿没阖眼,白天实在盯不住了才眯糊了仨半钟头。
两面墙山相撞,被害的影子倒在了地上。街对过的小旅店悬着给风撕破脸的广告牌,牌子下的白炽灯发出的昏黄的光斜打过来,妃子又往里挪了挪。手揣兜里,还得挤紧了羽绒服好堤防风往胸口里溜。可这没办法,谁让她贪便宜买打折货呢。这不还没新鲜几回,理所当然的拉锁坏了。
口罩被呼出的气体蒸湿又被十二月的风飕凉,妃子心里边怨怨的。
约摸九点多的街道上来往的人不是很多,也许不止是因为混凝土的路面儿经风干得不剩混凝只剩土。一辆三轮缓缓颠簸开来,给这寂而又寂的街道好歹添了点儿人声儿。妃子瞧见了,立马站起身。三轮车还没停稳当,就匆匆下来个同样戴口罩和墨镜穿裹的严严实实的男人。当然这些妃子看不到,她只注意到,男人比想象中胖了不少。
手机响了,短信提示音是高潮段的《多希望你在》,男人盯着屏幕,不是个陌生号码,“我这就过去”。
妃子听见自个儿兜里响起同样的铃声赶紧摁了查看,对着那个“嗯”愣怔了几秒。回过味儿来立刻把短信提示音设成了震动。手机屏幕散发出蓝幽幽的光,墙面上给岁月粉掉的白灰被映亮了,斑斑驳驳的烙在那里,是替老人们温习往昔,还是企图为年轻人们暗示未来?
妃子走过去,二十来米的距离走得象她二十多年的生活,温吞而拖沓。
男人的视线终于落到了妃子身上,眼见她愈走愈近,也不说话,点下头便往旅店里走。妃子目不转睛的瞅着男人的背影,一个不注意,羽绒服咧开了大嘴,风呼呼地往里灌,妃子心头凉了半截,她抬头望望那块褪了色但起码还算完整的广告牌,也跟了进去。
妃子没睡过旅店,走进去才发现和电视里看到的不一样,这里没有柜台,狭窄的过道里一张钢丝床占了大半显得更窄蹩。老板娘就盘腿坐在床上,围盖着两床白被里用得看不出是青是黄的褥子。男人在跟她讲价钱。
小寸的电视里放着不知什么电影,深棕色小柜边儿上的烟灰缸里积满烟灰,还斜插着几根烟蒂。电视后的墙上歪挂着插座,最白的那个插销直连老板娘屁股下的电褥子。如果她真的是老板娘的话。价钱似乎定下了,当然这根本没得改,不过是男人挑了间最便宜的那种。他从钱夹子里抽出几张半旧的十块,换回把钥匙。到底几张妃子没留意看,但她觉得有点不值,不过男人也有点儿抠,这也是实话。
老板娘又回头看她的电视了,顺便瞥了眼干杵在边儿上不出声儿也不跟男人闹的妃子。妃子说不清老板娘脸上是同情是瞧不起抑或是,很单纯的那种旁观的冷眼?她说不清,就是村里那些小伎俩的脸色她都读不懂,更何谈这样的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脸了。
妃子跟在男人后边儿,低着头瞅脚下淤满泥的楼梯的地砖缝,昏暗的光线甩在和刚才见过褥被里仿佛的墙壁上,让人有种进了地牢的幻觉。冷不防的,妃子被迎面下去的男人摸了把大腿,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那男的刚好下到拐角。他仰着肥硕的脑袋虎紧了脸嚷道:看什么看,没他妈见过啊。妃子想想还是算了。楼下,那个让她头皮发麻的嗓子又叫唤起来:我说老娘诶,总他妈得给我点零花的吧!
男人停在二楼最西头的房间前拧开锁待妃子走近前两人前后脚进了屋。男人不由地伸手去摸墙上的灯绳儿,妃子跟着抓到了他手,他也忆起来不该这么着于是作罢。气氛有点凝滞了,妃子不自在的把手伸进兜里,正好碰到她那急躁得震动的手机。妃子走出屋,见有俩未接电话和短信,都是她妈的手机号就发回短信去:在老同学家还不放心呀?人明儿就又回婆家了让我俩也好好说会话呗!
妃子见着“发送成功”的字样刚想进去又发过条短信这才关了机:等我也嫁给那个丑子,再想见面儿,猴年马月了。
男人坐在床上,拉开拉锁的声音有点儿刺耳。
窗帘略小了点,都覆不满正正方方的窗户,而且外头的路灯光能隐约透过来,至少妃子看得见男人脱了羽绒服正转过身来瞅着自己,好象在说:该你了。
男人躺在床上,听着下铺那位酣畅地打着呼噜。时间真快,转眼,他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夜晚有这位任兄的背景音乐。他又疑惑,不知道还习不习惯杜泽的呼噜声,从前那小子每回非得挨自己一拳才能消停会儿的。
另两个室友不知又去哪鬼混了,要是那个姓王的又喝个半死才回来,不可想象,不可想象。上上回反得我一直不知道荼縻竟然是一种小花,清雅的白色,淡然的芬芳,像一个女子心中的爱情,静寂的,内敛的,在内心寂寞地盛开--<林花谢了>妃子靠墙根蹲着,黑黑亮亮的眼睛淹没在这片儿地域的乌烟障气和墨镜的黑色投影里。说黑黑亮亮也不太对,昨天整宿没阖眼,白天实在盯不住了才眯糊了仨半钟头。
两面墙山相撞,被害的影子倒在了地上。街对过的小旅店悬着给风撕破脸的广告牌,牌子下的白炽灯发出的昏黄的光斜打过来,妃子又往里挪了挪。手揣兜里,还得挤紧了羽绒服好堤防风往胸口里溜。可这没办法,谁让她贪便宜买打折货呢。这不还没新鲜几回,理所当然的拉锁坏了。
口罩被呼出的气体蒸湿又被十二月的风飕凉,妃子心里边怨怨的。
约摸九点多的街道上来往的人不是很多,也许不止是因为混凝土的路面儿经风干得不剩混凝只剩土。一辆三轮缓缓颠簸开来,给这寂而又寂的街道好歹添了点儿人声儿。妃子瞧见了,立马站起身。三轮车还没停稳当,就匆匆下来个同样戴口罩和墨镜穿裹的严严实实的男人。当然这些妃子看不到,她只注意到,男人比想象中胖了不少。
手机响了,短信提示音是高潮段的《多希望你在》,男人盯着屏幕,不是个陌生号码,“我这就过去”。
妃子听见自个儿兜里响起同样的铃声赶紧摁了查看,对着那个“嗯”愣怔了几秒。回过味儿来立刻把短信提示音设成了震动。手机屏幕散发出蓝幽幽的光,墙面上给岁月粉掉的白灰被映亮了,斑斑驳驳的烙在那里,是替老人们温习往昔,还是企图为年轻人们暗示未来?
妃子走过去,二十来米的距离走得象她二十多年的生活,温吞而拖沓。
男人的视线终于落到了妃子身上,眼见她愈走愈近,也不说话,点下头便往旅店里走。妃子目不转睛的瞅着男人的背影,一个不注意,羽绒服咧开了大嘴,风呼呼地往里灌,妃子心头凉了半截,她抬头望望那块褪了色但起码还算完整的广告牌,也跟了进去。
妃子没睡过旅店,走进去才发现和电视里看到的不一样,这里没有柜台,狭窄的过道里一张钢丝床占了大半显得更窄蹩。老板娘就盘腿坐在床上,围盖着两床白被里用得看不出是青是黄的褥子。男人在跟她讲价钱。
小寸的电视里放着不知什么电影,深棕色小柜边儿上的烟灰缸里积满烟灰,还斜插着几根烟蒂。电视后的墙上歪挂着插座,最白的那个插销直连老板娘屁股下的电褥子。如果她真的是老板娘的话。价钱似乎定下了,当然这根本没得改,不过是男人挑了间最便宜的那种。他从钱夹子里抽出几张半旧的十块,换回把钥匙。到底几张妃子没留意看,但她觉得有点不值,不过男人也有点儿抠,这也是实话。
老板娘又回头看她的电视了,顺便瞥了眼干杵在边儿上不出声儿也不跟男人闹的妃子。妃子说不清老板娘脸上是同情是瞧不起抑或是,很单纯的那种旁观的冷眼?她说不清,就是村里那些小伎俩的脸色她都读不懂,更何谈这样的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脸了。
妃子跟在男人后边儿,低着头瞅脚下淤满泥的楼梯的地砖缝,昏暗的光线甩在和刚才见过褥被里仿佛的墙壁上,让人有种进了地牢的幻觉。冷不防的,妃子被迎面下去的男人摸了把大腿,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那男的刚好下到拐角。他仰着肥硕的脑袋虎紧了脸嚷道:看什么看,没他妈见过啊。妃子想想还是算了。楼下,那个让她头皮发麻的嗓子又叫唤起来:我说老娘诶,总他妈得给我点零花的吧!
男人停在二楼最西头的房间前拧开锁待妃子走近前两人前后脚进了屋。男人不由地伸手去摸墙上的灯绳儿,妃子跟着抓到了他手,他也忆起来不该这么着于是作罢。气氛有点凝滞了,妃子不自在的把手伸进兜里,正好碰到她那急躁得震动的手机。妃子走出屋,见有俩未接电话和短信,都是她妈的手机号就发回短信去:在老同学家还不放心呀?人明儿就又回婆家了让我俩也好好说会话呗!
妃子见着“发送成功”的字样刚想进去又发过条短信这才关了机:等我也嫁给那个丑子,再想见面儿,猴年马月了。
男人坐在床上,拉开拉锁的声音有点儿刺耳。
窗帘略小了点,都覆不满正正方方的窗户,而且外头的路灯光能隐约透过来,至少妃子看得见男人脱了羽绒服正转过身来瞅着自己,好象在说:该你了。
男人躺在床上,听着下铺那位酣畅地打着呼噜。时间真快,转眼,他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夜晚有这位任兄的背景音乐。他又疑惑,不知道还习不习惯杜泽的呼噜声,从前那小子每回非得挨自己一拳才能消停会儿的。
另两个室友不知又去哪鬼混了,要是那个姓王的又喝个半死才回来,不可想象,不可想象。上上回反得我一直不知道荼縻竟然是一种小花,清雅的白色,淡然的芬芳,像一个女子心中的爱情,静寂的,内敛的,在内心寂寞地盛开--<林花谢了>妃子靠墙根蹲着,黑黑亮亮的眼睛淹没在这片儿地域的乌烟障气和墨镜的黑色投影里。说黑黑亮亮也不太对,昨天整宿没阖眼,白天实在盯不住了才眯糊了仨半钟头。
两面墙山相撞,被害的影子倒在了地上。街对过的小旅店悬着给风撕破脸的广告牌,牌子下的白炽灯发出的昏黄的光斜打过来,妃子又往里挪了挪。手揣兜里,还得挤紧了羽绒服好堤防风往胸口里溜。可这没办法,谁让她贪便宜买打折货呢。这不还没新鲜几回,理所当然的拉锁坏了。
口罩被呼出的气体蒸湿又被十二月的风飕凉,妃子心里边怨怨的。
约摸九点多的街道上来往的人不是很多,也许不止是因为混凝土的路面儿经风干得不剩混凝只剩土。一辆三轮缓缓颠簸开来,给这寂而又寂的街道好歹添了点儿人声儿。妃子瞧见了,立马站起身。三轮车还没停稳当,就匆匆下来个同样戴口罩和墨镜穿裹的严严实实的男人。当然这些妃子看不到,她只注意到,男人比想象中胖了不少。
手机响了,短信提示音是高潮段的《多希望你在》,男人盯着屏幕,不是个陌生号码,“我这就过去”。
妃子听见自个儿兜里响起同样的铃声赶紧摁了查看,对着那个“嗯”愣怔了几秒。回过味儿来立刻把短信提示音设成了震动。手机屏幕散发出蓝幽幽的光,墙面上给岁月粉掉的白灰被映亮了,斑斑驳驳的烙在那里,是替老人们温习往昔,还是企图为年轻人们暗示未来?
妃子走过去,二十来米的距离走得象她二十多年的生活,温吞而拖沓。
男人的视线终于落到了妃子身上,眼见她愈走愈近,也不说话,点下头便往旅店里走。妃子目不转睛的瞅着男人的背影,一个不注意,羽绒服咧开了大嘴,风呼呼地往里灌,妃子心头凉了半截,她抬头望望那块褪了色但起码还算完整的广告牌,也跟了进去。
妃子没睡过旅店,走进去才发现和电视里看到的不一样,这里没有柜台,狭窄的过道里一张钢丝床占了大半显得更窄蹩。老板娘就盘腿坐在床上,围盖着两床白被里用得看不出是青是黄的褥子。男人在跟她讲价钱。
小寸的电视里放着不知什么电影,深棕色小柜边儿上的烟灰缸里积满烟灰,还斜插着几根烟蒂。电视后的墙上歪挂着插座,最白的那个插销直连老板娘屁股下的电褥子。如果她真的是老板娘的话。价钱似乎定下了,当然这根本没得改,不过是男人挑了间最便宜的那种。他从钱夹子里抽出几张半旧的十块,换回把钥匙。到底几张妃子没留意看,但她觉得有点不值,不过男人也有点儿抠,这也是实话。
老板娘又回头看她的电视了,顺便瞥了眼干杵在边儿上不出声儿也不跟男人闹的妃子。妃子说不清老板娘脸上是同情是瞧不起抑或是,很单纯的那种旁观的冷眼?她说不清,就是村里那些小伎俩的脸色她都读不懂,更何谈这样的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脸了。
妃子跟在男人后边儿,低着头瞅脚下淤满泥的楼梯的地砖缝,昏暗的光线甩在和刚才见过褥被里仿佛的墙壁上,让人有种进了地牢的幻觉。冷不防的,妃子被迎面下去的男人摸了把大腿,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那男的刚好下到拐角。他仰着肥硕的脑袋虎紧了脸嚷道:看什么看,没他妈见过啊。妃子想想还是算了。楼下,那个让她头皮发麻的嗓子又叫唤起来:我说老娘诶,总他妈得给我点零花的吧!
男人停在二楼最西头的房间前拧开锁待妃子走近前两人前后脚进了屋。男人不由地伸手去摸墙上的灯绳儿,妃子跟着抓到了他手,他也忆起来不该这么着于是作罢。气氛有点凝滞了,妃子不自在的把手伸进兜里,正好碰到她那急躁得震动的手机。妃子走出屋,见有俩未接电话和短信,都是她妈的手机号就发回短信去:在老同学家还不放心呀?人明儿就又回婆家了让我俩也好好说会话呗!
妃子见着“发送成功”的字样刚想进去又发过条短信这才关了机:等我也嫁给那个丑子,再想见面儿,猴年马月了。
男人坐在床上,拉开拉锁的声音有点儿刺耳。
窗帘略小了点,都覆不满正正方方的窗户,而且外头的路灯光能隐约透过来,至少妃子看得见男人脱了羽绒服正转过身来瞅着自己,好象在说:该你了。
男人躺在床上,听着下铺那位酣畅地打着呼噜。时间真快,转眼,他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夜晚有这位任兄的背景音乐。他又疑惑,不知道还习不习惯杜泽的呼噜声,从前那小子每回非得挨自己一拳才能消停会儿的。
另两个室友不知又去哪鬼混了,要是那个姓王的又喝个半死才回来,不可想象,不可想象。上上回反得我一直不知道荼縻竟然是一种小花,清雅的白色,淡然的芬芳,像一个女子心中的爱情,静寂的,内敛的,在内心寂寞地盛开--<林花谢了>妃子靠墙根蹲着,黑黑亮亮的眼睛淹没在这片儿地域的乌烟障气和墨镜的黑色投影里。说黑黑亮亮也不太对,昨天整宿没阖眼,白天实在盯不住了才眯糊了仨半钟头。
两面墙山相撞,被害的影子倒在了地上。街对过的小旅店悬着给风撕破脸的广告牌,牌子下的白炽灯发出的昏黄的光斜打过来,妃子又往里挪了挪。手揣兜里,还得挤紧了羽绒服好堤防风往胸口里溜。可这没办法,谁让她贪便宜买打折货呢。这不还没新鲜几回,理所当然的拉锁坏了。
口罩被呼出的气体蒸湿又被十二月的风飕凉,妃子心里边怨怨的。
约摸九点多的街道上来往的人不是很多,也许不止是因为混凝土的路面儿经风干得不剩混凝只剩土。一辆三轮缓缓颠簸开来,给这寂而又寂的街道好歹添了点儿人声儿。妃子瞧见了,立马站起身。三轮车还没停稳当,就匆匆下来个同样戴口罩和墨镜穿裹的严严实实的男人。当然这些妃子看不到,她只注意到,男人比想象中胖了不少。
手机响了,短信提示音是高潮段的《多希望你在》,男人盯着屏幕,不是个陌生号码,“我这就过去”。
妃子听见自个儿兜里响起同样的铃声赶紧摁了查看,对着那个“嗯”愣怔了几秒。回过味儿来立刻把短信提示音设成了震动。手机屏幕散发出蓝幽幽的光,墙面上给岁月粉掉的白灰被映亮了,斑斑驳驳的烙在那里,是替老人们温习往昔,还是企图为年轻人们暗示未来?
妃子走过去,二十来米的距离走得象她二十多年的生活,温吞而拖沓。
男人的视线终于落到了妃子身上,眼见她愈走愈近,也不说话,点下头便往旅店里走。妃子目不转睛的瞅着男人的背影,一个不注意,羽绒服咧开了大嘴,风呼呼地往里灌,妃子心头凉了半截,她抬头望望那块褪了色但起码还算完整的广告牌,也跟了进去。
妃子没睡过旅店,走进去才发现和电视里看到的不一样,这里没有柜台,狭窄的过道里一张钢丝床占了大半显得更窄蹩。老板娘就盘腿坐在床上,围盖着两床白被里用得看不出是青是黄的褥子。男人在跟她讲价钱。
小寸的电视里放着不知什么电影,深棕色小柜边儿上的烟灰缸里积满烟灰,还斜插着几根烟蒂。电视后的墙上歪挂着插座,最白的那个插销直连老板娘屁股下的电褥子。如果她真的是老板娘的话。价钱似乎定下了,当然这根本没得改,不过是男人挑了间最便宜的那种。他从钱夹子里抽出几张半旧的十块,换回把钥匙。到底几张妃子没留意看,但她觉得有点不值,不过男人也有点儿抠,这也是实话。
老板娘又回头看她的电视了,顺便瞥了眼干杵在边儿上不出声儿也不跟男人闹的妃子。妃子说不清老板娘脸上是同情是瞧不起抑或是,很单纯的那种旁观的冷眼?她说不清,就是村里那些小伎俩的脸色她都读不懂,更何谈这样的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脸了。
妃子跟在男人后边儿,低着头瞅脚下淤满泥的楼梯的地砖缝,昏暗的光线甩在和刚才见过褥被里仿佛的墙壁上,让人有种进了地牢的幻觉。冷不防的,妃子被迎面下去的男人摸了把大腿,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那男的刚好下到拐角。他仰着肥硕的脑袋虎紧了脸嚷道:看什么看,没他妈见过啊。妃子想想还是算了。楼下,那个让她头皮发麻的嗓子又叫唤起来:我说老娘诶,总他妈得给我点零花的吧!
男人停在二楼最西头的房间前拧开锁待妃子走近前两人前后脚进了屋。男人不由地伸手去摸墙上的灯绳儿,妃子跟着抓到了他手,他也忆起来不该这么着于是作罢。气氛有点凝滞了,妃子不自在的把手伸进兜里,正好碰到她那急躁得震动的手机。妃子走出屋,见有俩未接电话和短信,都是她妈的手机号就发回短信去:在老同学家还不放心呀?人明儿就又回婆家了让我俩也好好说会话呗!
妃子见着“发送成功”的字样刚想进去又发过条短信这才关了机:等我也嫁给那个丑子,再想见面儿,猴年马月了。
男人坐在床上,拉开拉锁的声音有点儿刺耳。
窗帘略小了点,都覆不满正正方方的窗户,而且外头的路灯光能隐约透过来,至少妃子看得见男人脱了羽绒服正转过身来瞅着自己,好象在说:该你了。
男人躺在床上,听着下铺那位酣畅地打着呼噜。时间真快,转眼,他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夜晚有这位任兄的背景音乐。他又疑惑,不知道还习不习惯杜泽的呼噜声,从前那小子每回非得挨自己一拳才能消停会儿的。
另两个室友不知又去哪鬼混了,要是那个姓王的又喝个半死才回来,不可想象,不可想象。上上回反得我一直不知道荼縻竟然是一种小花,清雅的白色,淡然的芬芳,像一个女子心中的爱情,静寂的,内敛的,在内心寂寞地盛开--<林花谢了>妃子靠墙根蹲着,黑黑亮亮的眼睛淹没在这片儿地域的乌烟障气和墨镜的黑色投影里。说黑黑亮亮也不太对,昨天整宿没阖眼,白天实在盯不住了才眯糊了仨半钟头。
两面墙山相撞,被害的影子倒在了地上。街对过的小旅店悬着给风撕破脸的广告牌,牌子下的白炽灯发出的昏黄的光斜打过来,妃子又往里挪了挪。手揣兜里,还得挤紧了羽绒服好堤防风往胸口里溜。可这没办法,谁让她贪便宜买打折货呢。这不还没新鲜几回,理所当然的拉锁坏了。
口罩被呼出的气体蒸湿又被十二月的风飕凉,妃子心里边怨怨的。
约摸九点多的街道上来往的人不是很多,也许不止是因为混凝土的路面儿经风干得不剩混凝只剩土。一辆三轮缓缓颠簸开来,给这寂而又寂的街道好歹添了点儿人声儿。妃子瞧见了,立马站起身。三轮车还没停稳当,就匆匆下来个同样戴口罩和墨镜穿裹的严严实实的男人。当然这些妃子看不到,她只注意到,男人比想象中胖了不少。
手机响了,短信提示音是高潮段的《多希望你在》,男人盯着屏幕,不是个陌生号码,“我这就过去”。
妃子听见自个儿兜里响起同样的铃声赶紧摁了查看,对着那个“嗯”愣怔了几秒。回过味儿来立刻把短信提示音设成了震动。手机屏幕散发出蓝幽幽的光,墙面上给岁月粉掉的白灰被映亮了,斑斑驳驳的烙在那里,是替老人们温习往昔,还是企图为年轻人们暗示未来?
妃子走过去,二十来米的距离走得象她二十多年的生活,温吞而拖沓。
男人的视线终于落到了妃子身上,眼见她愈走愈近,也不说话,点下头便往旅店里走。妃子目不转睛的瞅着男人的背影,一个不注意,羽绒服咧开了大嘴,风呼呼地往里灌,妃子心头凉了半截,她抬头望望那块褪了色但起码还算完整的广告牌,也跟了进去。
妃子没睡过旅店,走进去才发现和电视里看到的不一样,这里没有柜台,狭窄的过道里一张钢丝床占了大半显得更窄蹩。老板娘就盘腿坐在床上,围盖着两床白被里用得看不出是青是黄的褥子。男人在跟她讲价钱。
小寸的电视里放着不知什么电影,深棕色小柜边儿上的烟灰缸里积满烟灰,还斜插着几根烟蒂。电视后的墙上歪挂着插座,最白的那个插销直连老板娘屁股下的电褥子。如果她真的是老板娘的话。价钱似乎定下了,当然这根本没得改,不过是男人挑了间最便宜的那种。他从钱夹子里抽出几张半旧的十块,换回把钥匙。到底几张妃子没留意看,但她觉得有点不值,不过男人也有点儿抠,这也是实话。
老板娘又回头看她的电视了,顺便瞥了眼干杵在边儿上不出声儿也不跟男人闹的妃子。妃子说不清老板娘脸上是同情是瞧不起抑或是,很单纯的那种旁观的冷眼?她说不清,就是村里那些小伎俩的脸色她都读不懂,更何谈这样的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脸了。
妃子跟在男人后边儿,低着头瞅脚下淤满泥的楼梯的地砖缝,昏暗的光线甩在和刚才见过褥被里仿佛的墙壁上,让人有种进了地牢的幻觉。冷不防的,妃子被迎面下去的男人摸了把大腿,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那男的刚好下到拐角。他仰着肥硕的脑袋虎紧了脸嚷道:看什么看,没他妈见过啊。妃子想想还是算了。楼下,那个让她头皮发麻的嗓子又叫唤起来:我说老娘诶,总他妈得给我点零花的吧!
男人停在二楼最西头的房间前拧开锁待妃子走近前两人前后脚进了屋。男人不由地伸手去摸墙上的灯绳儿,妃子跟着抓到了他手,他也忆起来不该这么着于是作罢。气氛有点凝滞了,妃子不自在的把手伸进兜里,正好碰到她那急躁得震动的手机。妃子走出屋,见有俩未接电话和短信,都是她妈的手机号就发回短信去:在老同学家还不放心呀?人明儿就又回婆家了让我俩也好好说会话呗!
妃子见着“发送成功”的字样刚想进去又发过条短信这才关了机:等我也嫁给那个丑子,再想见面儿,猴年马月了。
男人坐在床上,拉开拉锁的声音有点儿刺耳。
窗帘略小了点,都覆不满正正方方的窗户,而且外头的路灯光能隐约透过来,至少妃子看得见男人脱了羽绒服正转过身来瞅着自己,好象在说:该你了。
男人躺在床上,听着下铺那位酣畅地打着呼噜。时间真快,转眼,他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夜晚有这位任兄的背景音乐。他又疑惑,不知道还习不习惯杜泽的呼噜声,从前那小子每回非得挨自己一拳才能消停会儿的。
另两个室友不知又去哪鬼混了,要是那个姓王的又喝个半死才回来,不可想象,不可想象。上上回反得我一直不知道荼縻竟然是一种小花,清雅的白色,淡然的芬芳,像一个女子心中的爱情,静寂的,内敛的,在内心寂寞地盛开--<林花谢了>妃子靠墙根蹲着,黑黑亮亮的眼睛淹没在这片儿地域的乌烟障气和墨镜的黑色投影里。说黑黑亮亮也不太对,昨天整宿没阖眼,白天实在盯不住了才眯糊了仨半钟头。
两面墙山相撞,被害的影子倒在了地上。街对过的小旅店悬着给风撕破脸的广告牌,牌子下的白炽灯发出的昏黄的光斜打过来,妃子又往里挪了挪。手揣兜里,还得挤紧了羽绒服好堤防风往胸口里溜。可这没办法,谁让她贪便宜买打折货呢。这不还没新鲜几回,理所当然的拉锁坏了。
口罩被呼出的气体蒸湿又被十二月的风飕凉,妃子心里边怨怨的。
约摸九点多的街道上来往的人不是很多,也许不止是因为混凝土的路面儿经风干得不剩混凝只剩土。一辆三轮缓缓颠簸开来,给这寂而又寂的街道好歹添了点儿人声儿。妃子瞧见了,立马站起身。三轮车还没停稳当,就匆匆下来个同样戴口罩和墨镜穿裹的严严实实的男人。当然这些妃子看不到,她只注意到,男人比想象中胖了不少。
手机响了,短信提示音是高潮段的《多希望你在》,男人盯着屏幕,不是个陌生号码,“我这就过去”。
妃子听见自个儿兜里响起同样的铃声赶紧摁了查看,对着那个“嗯”愣怔了几秒。回过味儿来立刻把短信提示音设成了震动。手机屏幕散发出蓝幽幽的光,墙面上给岁月粉掉的白灰被映亮了,斑斑驳驳的烙在那里,是替老人们温习往昔,还是企图为年轻人们暗示未来?
妃子走过去,二十来米的距离走得象她二十多年的生活,温吞而拖沓。
男人的视线终于落到了妃子身上,眼见她愈走愈近,也不说话,点下头便往旅店里走。妃子目不转睛的瞅着男人的背影,一个不注意,羽绒服咧开了大嘴,风呼呼地往里灌,妃子心头凉了半截,她抬头望望那块褪了色但起码还算完整的广告牌,也跟了进去。
妃子没睡过旅店,走进去才发现和电视里看到的不一样,这里没有柜台,狭窄的过道里一张钢丝床占了大半显得更窄蹩。老板娘就盘腿坐在床上,围盖着两床白被里用得看不出是青是黄的褥子。男人在跟她讲价钱。
小寸的电视里放着不知什么电影,深棕色小柜边儿上的烟灰缸里积满烟灰,还斜插着几根烟蒂。电视后的墙上歪挂着插座,最白的那个插销直连老板娘屁股下的电褥子。如果她真的是老板娘的话。价钱似乎定下了,当然这根本没得改,不过是男人挑了间最便宜的那种。他从钱夹子里抽出几张半旧的十块,换回把钥匙。到底几张妃子没留意看,但她觉得有点不值,不过男人也有点儿抠,这也是实话。
老板娘又回头看她的电视了,顺便瞥了眼干杵在边儿上不出声儿也不跟男人闹的妃子。妃子说不清老板娘脸上是同情是瞧不起抑或是,很单纯的那种旁观的冷眼?她说不清,就是村里那些小伎俩的脸色她都读不懂,更何谈这样的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脸了。
妃子跟在男人后边儿,低着头瞅脚下淤满泥的楼梯的地砖缝,昏暗的光线甩在和刚才见过褥被里仿佛的墙壁上,让人有种进了地牢的幻觉。冷不防的,妃子被迎面下去的男人摸了把大腿,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那男的刚好下到拐角。他仰着肥硕的脑袋虎紧了脸嚷道:看什么看,没他妈见过啊。妃子想想还是算了。楼下,那个让她头皮发麻的嗓子又叫唤起来:我说老娘诶,总他妈得给我点零花的吧!
男人停在二楼最西头的房间前拧开锁待妃子走近前两人前后脚进了屋。男人不由地伸手去摸墙上的灯绳儿,妃子跟着抓到了他手,他也忆起来不该这么着于是作罢。气氛有点凝滞了,妃子不自在的把手伸进兜里,正好碰到她那急躁得震动的手机。妃子走出屋,见有俩未接电话和短信,都是她妈的手机号就发回短信去:在老同学家还不放心呀?人明儿就又回婆家了让我俩也好好说会话呗!
妃子见着“发送成功”的字样刚想进去又发过条短信这才关了机:等我也嫁给那个丑子,再想见面儿,猴年马月了。
男人坐在床上,拉开拉锁的声音有点儿刺耳。
窗帘略小了点,都覆不满正正方方的窗户,而且外头的路灯光能隐约透过来,至少妃子看得见男人脱了羽绒服正转过身来瞅着自己,好象在说:该你了。
男人躺在床上,听着下铺那位酣畅地打着呼噜。时间真快,转眼,他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夜晚有这位任兄的背景音乐。他又疑惑,不知道还习不习惯杜泽的呼噜声,从前那小子每回非得挨自己一拳才能消停会儿的。
另两个室友不知又去哪鬼混了,要是那个姓王的又喝个半死才回来,不可想象,不可想象。上上回反得我一直不知道荼縻竟然是一种小花,清雅的白色,淡然的芬芳,像一个女子心中的爱情,静寂的,内敛的,在内心寂寞地盛开--<林花谢了>妃子靠墙根蹲着,黑黑亮亮的眼睛淹没在这片儿地域的乌烟障气和墨镜的黑色投影里。说黑黑亮亮也不太对,昨天整宿没阖眼,白天实在盯不住了才眯糊了仨半钟头。
两面墙山相撞,被害的影子倒在了地上。街对过的小旅店悬着给风撕破脸的广告牌,牌子下的白炽灯发出的昏黄的光斜打过来,妃子又往里挪了挪。手揣兜里,还得挤紧了羽绒服好堤防风往胸口里溜。可这没办法,谁让她贪便宜买打折货呢。这不还没新鲜几回,理所当然的拉锁坏了。
口罩被呼出的气体蒸湿又被十二月的风飕凉,妃子心里边怨怨的。
约摸九点多的街道上来往的人不是很多,也许不止是因为混凝土的路面儿经风干得不剩混凝只剩土。一辆三轮缓缓颠簸开来,给这寂而又寂的街道好歹添了点儿人声儿。妃子瞧见了,立马站起身。三轮车还没停稳当,就匆匆下来个同样戴口罩和墨镜穿裹的严严实实的男人。当然这些妃子看不到,她只注意到,男人比想象中胖了不少。
手机响了,短信提示音是高潮段的《多希望你在》,男人盯着屏幕,不是个陌生号码,“我这就过去”。
妃子听见自个儿兜里响起同样的铃声赶紧摁了查看,对着那个“嗯”愣怔了几秒。回过味儿来立刻把短信提示音设成了震动。手机屏幕散发出蓝幽幽的光,墙面上给岁月粉掉的白灰被映亮了,斑斑驳驳的烙在那里,是替老人们温习往昔,还是企图为年轻人们暗示未来?
妃子走过去,二十来米的距离走得象她二十多年的生活,温吞而拖沓。
男人的视线终于落到了妃子身上,眼见她愈走愈近,也不说话,点下头便往旅店里走。妃子目不转睛的瞅着男人的背影,一个不注意,羽绒服咧开了大嘴,风呼呼地往里灌,妃子心头凉了半截,她抬头望望那块褪了色但起码还算完整的广告牌,也跟了进去。
妃子没睡过旅店,走进去才发现和电视里看到的不一样,这里没有柜台,狭窄的过道里一张钢丝床占了大半显得更窄蹩。老板娘就盘腿坐在床上,围盖着两床白被里用得看不出是青是黄的褥子。男人在跟她讲价钱。
小寸的电视里放着不知什么电影,深棕色小柜边儿上的烟灰缸里积满烟灰,还斜插着几根烟蒂。电视后的墙上歪挂着插座,最白的那个插销直连老板娘屁股下的电褥子。如果她真的是老板娘的话。价钱似乎定下了,当然这根本没得改,不过是男人挑了间最便宜的那种。他从钱夹子里抽出几张半旧的十块,换回把钥匙。到底几张妃子没留意看,但她觉得有点不值,不过男人也有点儿抠,这也是实话。
老板娘又回头看她的电视了,顺便瞥了眼干杵在边儿上不出声儿也不跟男人闹的妃子。妃子说不清老板娘脸上是同情是瞧不起抑或是,很单纯的那种旁观的冷眼?她说不清,就是村里那些小伎俩的脸色她都读不懂,更何谈这样的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脸了。
妃子跟在男人后边儿,低着头瞅脚下淤满泥的楼梯的地砖缝,昏暗的光线甩在和刚才见过褥被里仿佛的墙壁上,让人有种进了地牢的幻觉。冷不防的,妃子被迎面下去的男人摸了把大腿,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那男的刚好下到拐角。他仰着肥硕的脑袋虎紧了脸嚷道:看什么看,没他妈见过啊。妃子想想还是算了。楼下,那个让她头皮发麻的嗓子又叫唤起来:我说老娘诶,总他妈得给我点零花的吧!
男人停在二楼最西头的房间前拧开锁待妃子走近前两人前后脚进了屋。男人不由地伸手去摸墙上的灯绳儿,妃子跟着抓到了他手,他也忆起来不该这么着于是作罢。气氛有点凝滞了,妃子不自在的把手伸进兜里,正好碰到她那急躁得震动的手机。妃子走出屋,见有俩未接电话和短信,都是她妈的手机号就发回短信去:在老同学家还不放心呀?人明儿就又回婆家了让我俩也好好说会话呗!
妃子见着“发送成功”的字样刚想进去又发过条短信这才关了机:等我也嫁给那个丑子,再想见面儿,猴年马月了。
男人坐在床上,拉开拉锁的声音有点儿刺耳。
窗帘略小了点,都覆不满正正方方的窗户,而且外头的路灯光能隐约透过来,至少妃子看得见男人脱了羽绒服正转过身来瞅着自己,好象在说:该你了。
男人躺在床上,听着下铺那位酣畅地打着呼噜。时间真快,转眼,他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夜晚有这位任兄的背景音乐。他又疑惑,不知道还习不习惯杜泽的呼噜声,从前那小子每回非得挨自己一拳才能消停会儿的。
另两个室友不知又去哪鬼混了,要是那个姓王的又喝个半死才回来,不可想象,不可想象。上上回反得

好文章,赞一下
982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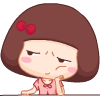
很一般,需努力
1082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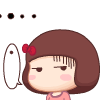
太差劲,踩一下
71人
- 上一篇:2010年的超级生活作文750字
- 下一篇:向着太阳奔跑作文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