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情杀手《2》 8500字
文章摘要:高中作文8500字:怎么写好灵情杀手《2》8500字作文?我溜目四顾,最后眼光停留在通往屋顶阁楼、那道封了尘的木门上,门上原封不动的尘积,显示搜屋者并没有上去,这也表明了对方的戒心不大,我也找不到窃听器一类的东西。取出开锁的工具,打开了木门,一道黑沉沉的楼梯,往上作六十度角伸延,陡斜异常。以下是丁香琳写的《灵情杀手《2》》范文;
好灵情杀手《2》作文8500字概况
- 作者:丁香琳
- 班级:高中高三
- 字数:8500字作文
- 体裁:
- 段落:分127段叙写
- 更新:2021年02月20日 10时21分
我溜目四顾,最后眼光停留在通往屋顶阁楼、那道封了尘的木门上,门上原封不动的尘积,显示搜屋者并没有上去,这也表明了对方的戒心不大,我也找不到窃听器一类的东西。
取出开锁的工具,打开了木门,一道黑沉沉的楼梯,往上作六十度角伸延,陡斜异常。
在门后找到了电灯的开关,但电灯却是坏了。
我亮着了电筒,走上楼梯。
脚下“嘎嘎”作响,我以手拔开封路的蛛网,屏着呼吸,忍受着身体移动惹起的飞扬尘屑。
终于跨过最后一组,一个四百多尺的空间呈现眼前。
没有任何家私杂物,只有一个巨型的三脚钢琴,一张长方形的琴凳,和一个被木板封了的窗。
奇怪的念头在我心中升起,楼梯这么窄小,爵士如何将这琴运上来?唯一的方法或者是从大窗吊上来,那还必须拆了部分墙壁,谁会做此蠢事,为何不干脆将它放在楼下的大厅里?
我走到琴旁,用电筒仔细地照射。
巨型琴浑体呈深红色,其间透着点点奇异的金光,就像给洒上了金粉,我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木质。
更奇怪的是这琴并没有被任何东西包起或掩盖,但琴身却不见一点尘屑。
心中一动,环目四顾,这里和蛛网封路的楼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竟然见不到一个蛛网、一点尘屑,也没有任何蟑螂、老鼠一类在这环境里的必有产品。
我伸手在琴身触摸。
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心中泛起。
心中暖洋洋的。
一股热流从琴身流注进我体里,又从我体里倒流回去,好象有点东西送到了我那里,也带走了一点东西。
我大骇缩手,在我的杀人生涯里,从未试过似此刻般地失去冷静。
阁楼一片寂静。
奇怪在这密封的空间并没有腐败空气的味道,也没有气闷的感觉,可是我并没有发现此一目了然的地方有任何通气的设备。
一切是如此平和静宁。
却又是如斯怪异诡奇。
我不甘心地再碰触琴身。这次奇怪的暖流没有了,难道刚才只是幻觉?
琴身出奇地冰凉,木质柔软温润,照理这是并不适合作琴身的材料。我对木材并不在行,不知这是什么木料。
我走到用木板封闭了的窗前,关掉了电筒,一束柔和的暗弱光线,从封窗的其中一块缺了边角的木板透射入来,破洞刚好看到俱乐部的正门,角度比楼下更理想,我计算子弹射出的位置,穿进目标的身体部分。
“叮!”
我整个人吓得跳了起来。
琴竟自动响起来。
不!绝不会是鬼魂,我是个无鬼论者。
我头皮发麻地看着像怪物般立在房中间的三脚琴。
我虽杀人无数,但被杀者都是匪徒、毒枭、恐怖分子等该杀的人,这是隐身人的原则,这些凶徒轻松地在法网外逍遥自在,正需要有我这类不受约束的执法者给以处决。
但在我眼前的却又是活生生难以解释的现实。
我深吸一口气,往钢琴走去。
真怕它忽地又响奏起来,那时我应怎么办?
没有任何事发生,我小心地掀起覆着琴键的盖子,一长列雪白的琴健现在眼前。
我伸手下去,手指轻动,叩了几个清音,只觉得琴音像响起自遥不可触的远处,心中兴起了一种平和宁静的感觉。
我多少年没有听人弹琴了?
这些年来,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冷血无情,举凡和情绪有关的东西,我都避则不碰,音乐是其中之一。
每次杀人之后,我都找个地方花天酒地,狂玩女人,然后弃之如敝屣,只有那样才可使我松驰下来。
犹记得母亲最喜弹琴。她常弹奏的那小调已久被遗忘,忽然间又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活跃起来。我像是看到永不剪发的母亲,垂着乌黑的长发,阳光从她身侧的大窗透进来,将她侧脸就线条分明,但细节模糊的轮廓。
但母亲已死了。
在一次银行的械劫案中,成为了被牺牲的人质,匪徒枪杀她时,我离她只有尺半,她的手还拉着我。
她整个头爆裂开来 我溜目四顾,最后眼光停留在通往屋顶阁楼、那道封了尘的木门上,门上原封不动的尘积,显示搜屋者并没有上去,这也表明了对方的戒心不大,我也找不到窃听器一类的东西。取出开锁的工具,打开了木门,一道黑沉沉的楼梯,往上作六十度角伸延,陡斜异常。
在门后找到了电灯的开关,但电灯却是坏了。
我亮着了电筒,走上楼梯。
脚下“嘎嘎”作响,我以手拔开封路的蛛网,屏着呼吸,忍受着身体移动惹起的飞扬尘屑。
终于跨过最后一组,一个四百多尺的空间呈现眼前。
没有任何家私杂物,只有一个巨型的三脚钢琴,一张长方形的琴凳,和一个被木板封了的窗。
奇怪的念头在我心中升起,楼梯这么窄小,爵士如何将这琴运上来?唯一的方法或者是从大窗吊上来,那还必须拆了部分墙壁,谁会做此蠢事,为何不干脆将它放在楼下的大厅里?
我走到琴旁,用电筒仔细地照射。
巨型琴浑体呈深红色,其间透着点点奇异的金光,就像给洒上了金粉,我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木质。
更奇怪的是这琴并没有被任何东西包起或掩盖,但琴身却不见一点尘屑。
心中一动,环目四顾,这里和蛛网封路的楼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竟然见不到一个蛛网、一点尘屑,也没有任何蟑螂、老鼠一类在这环境里的必有产品。
我伸手在琴身触摸。
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心中泛起。
心中暖洋洋的。
一股热流从琴身流注进我体里,又从我体里倒流回去,好象有点东西送到了我那里,也带走了一点东西。
我大骇缩手,在我的杀人生涯里,从未试过似此刻般地失去冷静。
阁楼一片寂静。
奇怪在这密封的空间并没有腐败空气的味道,也没有气闷的感觉,可是我并没有发现此一目了然的地方有任何通气的设备。
一切是如此平和静宁。
却又是如斯怪异诡奇。
我不甘心地再碰触琴身。这次奇怪的暖流没有了,难道刚才只是幻觉?
琴身出奇地冰凉,木质柔软温润,照理这是并不适合作琴身的材料。我对木材并不在行,不知这是什么木料。
我走到用木板封闭了的窗前,关掉了电筒,一束柔和的暗弱光线,从封窗的其中一块缺了边角的木板透射入来,破洞刚好看到俱乐部的正门,角度比楼下更理想,我计算子弹射出的位置,穿进目标的身体部分。
“叮!”
我整个人吓得跳了起来。
琴竟自动响起来。
不!绝不会是鬼魂,我是个无鬼论者。
我头皮发麻地看着像怪物般立在房中间的三脚琴。
我虽杀人无数,但被杀者都是匪徒、毒枭、恐怖分子等该杀的人,这是隐身人的原则,这些凶徒轻松地在法网外逍遥自在,正需要有我这类不受约束的执法者给以处决。
但在我眼前的却又是活生生难以解释的现实。
我深吸一口气,往钢琴走去。
真怕它忽地又响奏起来,那时我应怎么办?
没有任何事发生,我小心地掀起覆着琴键的盖子,一长列雪白的琴健现在眼前。
我伸手下去,手指轻动,叩了几个清音,只觉得琴音像响起自遥不可触的远处,心中兴起了一种平和宁静的感觉。
我多少年没有听人弹琴了?
这些年来,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冷血无情,举凡和情绪有关的东西,我都避则不碰,音乐是其中之一。
每次杀人之后,我都找个地方花天酒地,狂玩女人,然后弃之如敝屣,只有那样才可使我松驰下来。
犹记得母亲最喜弹琴。她常弹奏的那小调已久被遗忘,忽然间又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活跃起来。我像是看到永不剪发的母亲,垂着乌黑的长发,阳光从她身侧的大窗透进来,将她侧脸就线条分明,但细节模糊的轮廓。
但母亲已死了。
在一次银行的械劫案中,成为了被牺牲的人质,匪徒枪杀她时,我离她只有尺半,她的手还拉着我。
她整个头爆裂开来 我溜目四顾,最后眼光停留在通往屋顶阁楼、那道封了尘的木门上,门上原封不动的尘积,显示搜屋者并没有上去,这也表明了对方的戒心不大,我也找不到窃听器一类的东西。取出开锁的工具,打开了木门,一道黑沉沉的楼梯,往上作六十度角伸延,陡斜异常。
在门后找到了电灯的开关,但电灯却是坏了。
我亮着了电筒,走上楼梯。
脚下“嘎嘎”作响,我以手拔开封路的蛛网,屏着呼吸,忍受着身体移动惹起的飞扬尘屑。
终于跨过最后一组,一个四百多尺的空间呈现眼前。
没有任何家私杂物,只有一个巨型的三脚钢琴,一张长方形的琴凳,和一个被木板封了的窗。
奇怪的念头在我心中升起,楼梯这么窄小,爵士如何将这琴运上来?唯一的方法或者是从大窗吊上来,那还必须拆了部分墙壁,谁会做此蠢事,为何不干脆将它放在楼下的大厅里?
我走到琴旁,用电筒仔细地照射。
巨型琴浑体呈深红色,其间透着点点奇异的金光,就像给洒上了金粉,我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木质。
更奇怪的是这琴并没有被任何东西包起或掩盖,但琴身却不见一点尘屑。
心中一动,环目四顾,这里和蛛网封路的楼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竟然见不到一个蛛网、一点尘屑,也没有任何蟑螂、老鼠一类在这环境里的必有产品。
我伸手在琴身触摸。
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心中泛起。
心中暖洋洋的。
一股热流从琴身流注进我体里,又从我体里倒流回去,好象有点东西送到了我那里,也带走了一点东西。
我大骇缩手,在我的杀人生涯里,从未试过似此刻般地失去冷静。
阁楼一片寂静。
奇怪在这密封的空间并没有腐败空气的味道,也没有气闷的感觉,可是我并没有发现此一目了然的地方有任何通气的设备。
一切是如此平和静宁。
却又是如斯怪异诡奇。
我不甘心地再碰触琴身。这次奇怪的暖流没有了,难道刚才只是幻觉?
琴身出奇地冰凉,木质柔软温润,照理这是并不适合作琴身的材料。我对木材并不在行,不知这是什么木料。
我走到用木板封闭了的窗前,关掉了电筒,一束柔和的暗弱光线,从封窗的其中一块缺了边角的木板透射入来,破洞刚好看到俱乐部的正门,角度比楼下更理想,我计算子弹射出的位置,穿进目标的身体部分。
“叮!”
我整个人吓得跳了起来。
琴竟自动响起来。
不!绝不会是鬼魂,我是个无鬼论者。
我头皮发麻地看着像怪物般立在房中间的三脚琴。
我虽杀人无数,但被杀者都是匪徒、毒枭、恐怖分子等该杀的人,这是隐身人的原则,这些凶徒轻松地在法网外逍遥自在,正需要有我这类不受约束的执法者给以处决。
但在我眼前的却又是活生生难以解释的现实。
我深吸一口气,往钢琴走去。
真怕它忽地又响奏起来,那时我应怎么办?
没有任何事发生,我小心地掀起覆着琴键的盖子,一长列雪白的琴健现在眼前。
我伸手下去,手指轻动,叩了几个清音,只觉得琴音像响起自遥不可触的远处,心中兴起了一种平和宁静的感觉。
我多少年没有听人弹琴了?
这些年来,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冷血无情,举凡和情绪有关的东西,我都避则不碰,音乐是其中之一。
每次杀人之后,我都找个地方花天酒地,狂玩女人,然后弃之如敝屣,只有那样才可使我松驰下来。
犹记得母亲最喜弹琴。她常弹奏的那小调已久被遗忘,忽然间又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活跃起来。我像是看到永不剪发的母亲,垂着乌黑的长发,阳光从她身侧的大窗透进来,将她侧脸就线条分明,但细节模糊的轮廓。
但母亲已死了。
在一次银行的械劫案中,成为了被牺牲的人质,匪徒枪杀她时,我离她只有尺半,她的手还拉着我。
她整个头爆裂开来 我溜目四顾,最后眼光停留在通往屋顶阁楼、那道封了尘的木门上,门上原封不动的尘积,显示搜屋者并没有上去,这也表明了对方的戒心不大,我也找不到窃听器一类的东西。取出开锁的工具,打开了木门,一道黑沉沉的楼梯,往上作六十度角伸延,陡斜异常。
在门后找到了电灯的开关,但电灯却是坏了。
我亮着了电筒,走上楼梯。
脚下“嘎嘎”作响,我以手拔开封路的蛛网,屏着呼吸,忍受着身体移动惹起的飞扬尘屑。
终于跨过最后一组,一个四百多尺的空间呈现眼前。
没有任何家私杂物,只有一个巨型的三脚钢琴,一张长方形的琴凳,和一个被木板封了的窗。
奇怪的念头在我心中升起,楼梯这么窄小,爵士如何将这琴运上来?唯一的方法或者是从大窗吊上来,那还必须拆了部分墙壁,谁会做此蠢事,为何不干脆将它放在楼下的大厅里?
我走到琴旁,用电筒仔细地照射。
巨型琴浑体呈深红色,其间透着点点奇异的金光,就像给洒上了金粉,我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木质。
更奇怪的是这琴并没有被任何东西包起或掩盖,但琴身却不见一点尘屑。
心中一动,环目四顾,这里和蛛网封路的楼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竟然见不到一个蛛网、一点尘屑,也没有任何蟑螂、老鼠一类在这环境里的必有产品。
我伸手在琴身触摸。
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心中泛起。
心中暖洋洋的。
一股热流从琴身流注进我体里,又从我体里倒流回去,好象有点东西送到了我那里,也带走了一点东西。
我大骇缩手,在我的杀人生涯里,从未试过似此刻般地失去冷静。
阁楼一片寂静。
奇怪在这密封的空间并没有腐败空气的味道,也没有气闷的感觉,可是我并没有发现此一目了然的地方有任何通气的设备。
一切是如此平和静宁。
却又是如斯怪异诡奇。
我不甘心地再碰触琴身。这次奇怪的暖流没有了,难道刚才只是幻觉?
琴身出奇地冰凉,木质柔软温润,照理这是并不适合作琴身的材料。我对木材并不在行,不知这是什么木料。
我走到用木板封闭了的窗前,关掉了电筒,一束柔和的暗弱光线,从封窗的其中一块缺了边角的木板透射入来,破洞刚好看到俱乐部的正门,角度比楼下更理想,我计算子弹射出的位置,穿进目标的身体部分。
“叮!”
我整个人吓得跳了起来。
琴竟自动响起来。
不!绝不会是鬼魂,我是个无鬼论者。
我头皮发麻地看着像怪物般立在房中间的三脚琴。
我虽杀人无数,但被杀者都是匪徒、毒枭、恐怖分子等该杀的人,这是隐身人的原则,这些凶徒轻松地在法网外逍遥自在,正需要有我这类不受约束的执法者给以处决。
但在我眼前的却又是活生生难以解释的现实。
我深吸一口气,往钢琴走去。
真怕它忽地又响奏起来,那时我应怎么办?
没有任何事发生,我小心地掀起覆着琴键的盖子,一长列雪白的琴健现在眼前。
我伸手下去,手指轻动,叩了几个清音,只觉得琴音像响起自遥不可触的远处,心中兴起了一种平和宁静的感觉。
我多少年没有听人弹琴了?
这些年来,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冷血无情,举凡和情绪有关的东西,我都避则不碰,音乐是其中之一。
每次杀人之后,我都找个地方花天酒地,狂玩女人,然后弃之如敝屣,只有那样才可使我松驰下来。
犹记得母亲最喜弹琴。她常弹奏的那小调已久被遗忘,忽然间又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活跃起来。我像是看到永不剪发的母亲,垂着乌黑的长发,阳光从她身侧的大窗透进来,将她侧脸就线条分明,但细节模糊的轮廓。
但母亲已死了。
在一次银行的械劫案中,成为了被牺牲的人质,匪徒枪杀她时,我离她只有尺半,她的手还拉着我。
她整个头爆裂开来 我溜目四顾,最后眼光停留在通往屋顶阁楼、那道封了尘的木门上,门上原封不动的尘积,显示搜屋者并没有上去,这也表明了对方的戒心不大,我也找不到窃听器一类的东西。取出开锁的工具,打开了木门,一道黑沉沉的楼梯,往上作六十度角伸延,陡斜异常。
在门后找到了电灯的开关,但电灯却是坏了。
我亮着了电筒,走上楼梯。
脚下“嘎嘎”作响,我以手拔开封路的蛛网,屏着呼吸,忍受着身体移动惹起的飞扬尘屑。
终于跨过最后一组,一个四百多尺的空间呈现眼前。
没有任何家私杂物,只有一个巨型的三脚钢琴,一张长方形的琴凳,和一个被木板封了的窗。
奇怪的念头在我心中升起,楼梯这么窄小,爵士如何将这琴运上来?唯一的方法或者是从大窗吊上来,那还必须拆了部分墙壁,谁会做此蠢事,为何不干脆将它放在楼下的大厅里?
我走到琴旁,用电筒仔细地照射。
巨型琴浑体呈深红色,其间透着点点奇异的金光,就像给洒上了金粉,我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木质。
更奇怪的是这琴并没有被任何东西包起或掩盖,但琴身却不见一点尘屑。
心中一动,环目四顾,这里和蛛网封路的楼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竟然见不到一个蛛网、一点尘屑,也没有任何蟑螂、老鼠一类在这环境里的必有产品。
我伸手在琴身触摸。
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心中泛起。
心中暖洋洋的。
一股热流从琴身流注进我体里,又从我体里倒流回去,好象有点东西送到了我那里,也带走了一点东西。
我大骇缩手,在我的杀人生涯里,从未试过似此刻般地失去冷静。
阁楼一片寂静。
奇怪在这密封的空间并没有腐败空气的味道,也没有气闷的感觉,可是我并没有发现此一目了然的地方有任何通气的设备。
一切是如此平和静宁。
却又是如斯怪异诡奇。
我不甘心地再碰触琴身。这次奇怪的暖流没有了,难道刚才只是幻觉?
琴身出奇地冰凉,木质柔软温润,照理这是并不适合作琴身的材料。我对木材并不在行,不知这是什么木料。
我走到用木板封闭了的窗前,关掉了电筒,一束柔和的暗弱光线,从封窗的其中一块缺了边角的木板透射入来,破洞刚好看到俱乐部的正门,角度比楼下更理想,我计算子弹射出的位置,穿进目标的身体部分。
“叮!”
我整个人吓得跳了起来。
琴竟自动响起来。
不!绝不会是鬼魂,我是个无鬼论者。
我头皮发麻地看着像怪物般立在房中间的三脚琴。
我虽杀人无数,但被杀者都是匪徒、毒枭、恐怖分子等该杀的人,这是隐身人的原则,这些凶徒轻松地在法网外逍遥自在,正需要有我这类不受约束的执法者给以处决。
但在我眼前的却又是活生生难以解释的现实。
我深吸一口气,往钢琴走去。
真怕它忽地又响奏起来,那时我应怎么办?
没有任何事发生,我小心地掀起覆着琴键的盖子,一长列雪白的琴健现在眼前。
我伸手下去,手指轻动,叩了几个清音,只觉得琴音像响起自遥不可触的远处,心中兴起了一种平和宁静的感觉。
我多少年没有听人弹琴了?
这些年来,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冷血无情,举凡和情绪有关的东西,我都避则不碰,音乐是其中之一。
每次杀人之后,我都找个地方花天酒地,狂玩女人,然后弃之如敝屣,只有那样才可使我松驰下来。
犹记得母亲最喜弹琴。她常弹奏的那小调已久被遗忘,忽然间又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活跃起来。我像是看到永不剪发的母亲,垂着乌黑的长发,阳光从她身侧的大窗透进来,将她侧脸就线条分明,但细节模糊的轮廓。
但母亲已死了。
在一次银行的械劫案中,成为了被牺牲的人质,匪徒枪杀她时,我离她只有尺半,她的手还拉着我。
她整个头爆裂开来 我溜目四顾,最后眼光停留在通往屋顶阁楼、那道封了尘的木门上,门上原封不动的尘积,显示搜屋者并没有上去,这也表明了对方的戒心不大,我也找不到窃听器一类的东西。取出开锁的工具,打开了木门,一道黑沉沉的楼梯,往上作六十度角伸延,陡斜异常。
在门后找到了电灯的开关,但电灯却是坏了。
我亮着了电筒,走上楼梯。
脚下“嘎嘎”作响,我以手拔开封路的蛛网,屏着呼吸,忍受着身体移动惹起的飞扬尘屑。
终于跨过最后一组,一个四百多尺的空间呈现眼前。
没有任何家私杂物,只有一个巨型的三脚钢琴,一张长方形的琴凳,和一个被木板封了的窗。
奇怪的念头在我心中升起,楼梯这么窄小,爵士如何将这琴运上来?唯一的方法或者是从大窗吊上来,那还必须拆了部分墙壁,谁会做此蠢事,为何不干脆将它放在楼下的大厅里?
我走到琴旁,用电筒仔细地照射。
巨型琴浑体呈深红色,其间透着点点奇异的金光,就像给洒上了金粉,我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木质。
更奇怪的是这琴并没有被任何东西包起或掩盖,但琴身却不见一点尘屑。
心中一动,环目四顾,这里和蛛网封路的楼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竟然见不到一个蛛网、一点尘屑,也没有任何蟑螂、老鼠一类在这环境里的必有产品。
我伸手在琴身触摸。
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心中泛起。
心中暖洋洋的。
一股热流从琴身流注进我体里,又从我体里倒流回去,好象有点东西送到了我那里,也带走了一点东西。
我大骇缩手,在我的杀人生涯里,从未试过似此刻般地失去冷静。
阁楼一片寂静。
奇怪在这密封的空间并没有腐败空气的味道,也没有气闷的感觉,可是我并没有发现此一目了然的地方有任何通气的设备。
一切是如此平和静宁。
却又是如斯怪异诡奇。
我不甘心地再碰触琴身。这次奇怪的暖流没有了,难道刚才只是幻觉?
琴身出奇地冰凉,木质柔软温润,照理这是并不适合作琴身的材料。我对木材并不在行,不知这是什么木料。
我走到用木板封闭了的窗前,关掉了电筒,一束柔和的暗弱光线,从封窗的其中一块缺了边角的木板透射入来,破洞刚好看到俱乐部的正门,角度比楼下更理想,我计算子弹射出的位置,穿进目标的身体部分。
“叮!”
我整个人吓得跳了起来。
琴竟自动响起来。
不!绝不会是鬼魂,我是个无鬼论者。
我头皮发麻地看着像怪物般立在房中间的三脚琴。
我虽杀人无数,但被杀者都是匪徒、毒枭、恐怖分子等该杀的人,这是隐身人的原则,这些凶徒轻松地在法网外逍遥自在,正需要有我这类不受约束的执法者给以处决。
但在我眼前的却又是活生生难以解释的现实。
我深吸一口气,往钢琴走去。
真怕它忽地又响奏起来,那时我应怎么办?
没有任何事发生,我小心地掀起覆着琴键的盖子,一长列雪白的琴健现在眼前。
我伸手下去,手指轻动,叩了几个清音,只觉得琴音像响起自遥不可触的远处,心中兴起了一种平和宁静的感觉。
我多少年没有听人弹琴了?
这些年来,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冷血无情,举凡和情绪有关的东西,我都避则不碰,音乐是其中之一。
每次杀人之后,我都找个地方花天酒地,狂玩女人,然后弃之如敝屣,只有那样才可使我松驰下来。
犹记得母亲最喜弹琴。她常弹奏的那小调已久被遗忘,忽然间又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活跃起来。我像是看到永不剪发的母亲,垂着乌黑的长发,阳光从她身侧的大窗透进来,将她侧脸就线条分明,但细节模糊的轮廓。
但母亲已死了。
在一次银行的械劫案中,成为了被牺牲的人质,匪徒枪杀她时,我离她只有尺半,她的手还拉着我。
她整个头爆裂开来 我溜目四顾,最后眼光停留在通往屋顶阁楼、那道封了尘的木门上,门上原封不动的尘积,显示搜屋者并没有上去,这也表明了对方的戒心不大,我也找不到窃听器一类的东西。取出开锁的工具,打开了木门,一道黑沉沉的楼梯,往上作六十度角伸延,陡斜异常。
在门后找到了电灯的开关,但电灯却是坏了。
我亮着了电筒,走上楼梯。
脚下“嘎嘎”作响,我以手拔开封路的蛛网,屏着呼吸,忍受着身体移动惹起的飞扬尘屑。
终于跨过最后一组,一个四百多尺的空间呈现眼前。
没有任何家私杂物,只有一个巨型的三脚钢琴,一张长方形的琴凳,和一个被木板封了的窗。
奇怪的念头在我心中升起,楼梯这么窄小,爵士如何将这琴运上来?唯一的方法或者是从大窗吊上来,那还必须拆了部分墙壁,谁会做此蠢事,为何不干脆将它放在楼下的大厅里?
我走到琴旁,用电筒仔细地照射。
巨型琴浑体呈深红色,其间透着点点奇异的金光,就像给洒上了金粉,我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木质。
更奇怪的是这琴并没有被任何东西包起或掩盖,但琴身却不见一点尘屑。
心中一动,环目四顾,这里和蛛网封路的楼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竟然见不到一个蛛网、一点尘屑,也没有任何蟑螂、老鼠一类在这环境里的必有产品。
我伸手在琴身触摸。
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心中泛起。
心中暖洋洋的。
一股热流从琴身流注进我体里,又从我体里倒流回去,好象有点东西送到了我那里,也带走了一点东西。
我大骇缩手,在我的杀人生涯里,从未试过似此刻般地失去冷静。
阁楼一片寂静。
奇怪在这密封的空间并没有腐败空气的味道,也没有气闷的感觉,可是我并没有发现此一目了然的地方有任何通气的设备。
一切是如此平和静宁。
却又是如斯怪异诡奇。
我不甘心地再碰触琴身。这次奇怪的暖流没有了,难道刚才只是幻觉?
琴身出奇地冰凉,木质柔软温润,照理这是并不适合作琴身的材料。我对木材并不在行,不知这是什么木料。
我走到用木板封闭了的窗前,关掉了电筒,一束柔和的暗弱光线,从封窗的其中一块缺了边角的木板透射入来,破洞刚好看到俱乐部的正门,角度比楼下更理想,我计算子弹射出的位置,穿进目标的身体部分。
“叮!”
我整个人吓得跳了起来。
琴竟自动响起来。
不!绝不会是鬼魂,我是个无鬼论者。
我头皮发麻地看着像怪物般立在房中间的三脚琴。
我虽杀人无数,但被杀者都是匪徒、毒枭、恐怖分子等该杀的人,这是隐身人的原则,这些凶徒轻松地在法网外逍遥自在,正需要有我这类不受约束的执法者给以处决。
但在我眼前的却又是活生生难以解释的现实。
我深吸一口气,往钢琴走去。
真怕它忽地又响奏起来,那时我应怎么办?
没有任何事发生,我小心地掀起覆着琴键的盖子,一长列雪白的琴健现在眼前。
我伸手下去,手指轻动,叩了几个清音,只觉得琴音像响起自遥不可触的远处,心中兴起了一种平和宁静的感觉。
我多少年没有听人弹琴了?
这些年来,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冷血无情,举凡和情绪有关的东西,我都避则不碰,音乐是其中之一。
每次杀人之后,我都找个地方花天酒地,狂玩女人,然后弃之如敝屣,只有那样才可使我松驰下来。
犹记得母亲最喜弹琴。她常弹奏的那小调已久被遗忘,忽然间又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活跃起来。我像是看到永不剪发的母亲,垂着乌黑的长发,阳光从她身侧的大窗透进来,将她侧脸就线条分明,但细节模糊的轮廓。
但母亲已死了。
在一次银行的械劫案中,成为了被牺牲的人质,匪徒枪杀她时,我离她只有尺半,她的手还拉着我。
她整个头爆裂开来

好文章,赞一下
963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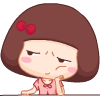
很一般,需努力
5063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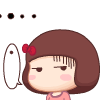
太差劲,踩一下
52人
- 上一篇:寂寞作文100字
- 下一篇:太阳能汽车作文4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