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前 10000字
文章摘要:高三作文10000字:怎么写好一路向前10000字作文?我对面坐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有二十多年的军龄,刚从北京探亲回来。我们在吃泡面。我把我带来的泡菜递给他,他便很豪爽地接过然后用叉子将其往面桶里扒。热腾腾的水汽和着酸辣的气味弥漫得浓浓。小玉和于博在个一个小娃儿画像,周围便聚拢了几个神色怡然的观众。以下是胡光民写的《一路向前》范文;
好一路向前作文10000字概况
- 作者:胡光民
- 班级:高中高三
- 字数:10000字作文
- 体裁:
- 段落:分36段叙写
- 更新:2021年01月23日 12时43分
我对面坐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有二十多年的军龄,刚从北京探亲回来。我们在吃泡面。我把我带来的泡菜递给他,他便很豪爽地接过然后用叉子将其往面桶里扒。热腾腾的水汽和着酸辣的气味弥漫得浓浓。小玉和于博在个一个小娃儿画像,周围便聚拢了几个神色怡然的观众。在我们座前的一个座,一个穿金戴银的老婆婆很洋气地向一个戴眼镜的老大爷神叨她已经游览了多少个城市。整节车厢就属我们这一块最热闹。
这列火车从北京开向成都,车上几乎全是四川人,各个都豪放得很。我对面那个男人一眼就看出我是学美术的。他说:“反正不象跳舞的,你身上有这个(美术)的气质。”我表面嬉笑,想想还真是变着戏法说我邋遢。窗外险山峻陵,阳光明晃却依旧雾气溟朦。又到了秦岭。二零零七年三月八号,我在回家的路上。
老张的画室在五道口一座简朴的宿舍楼里,跟全北京数不胜数的画室比起来,这画室的规模可能就算最小的了。这话是老张自己说的。确实,人家101画室那叫一个“大”,一天光请的模特儿就比咱画室的人还多。可牛皮不是吹的,我们是一支精良的可以打硬仗的特种部队,铆足了劲儿干活那阵仗便是练就真工夫的基础。之所以叫干活,因为大凡学这个的人都晓得这原本是不能跟艺术挂多大钩的(犹如高考作文与文学的关系),又之所以拼命,因为大凡学这个的人都晓得考上心目中那所学校不是光靠运气就可以完事的。我们都是要雄赳赳、气昂昂地挺过鸭绿江的。
我们画室离清华大学太近了。我去“SevenEleven "买泡面时一不小心抬头便远远回收了那座四平八稳建筑的影象。中午我在“重庆小吃”吃鱼香肉丝饭时,老板用重庆话对我说:“那个小伙子也是清华的。在这座楼里打工。”老板用手指了指我身后的那座煞是金碧辉煌的银谷大厦。小伙子似乎是听到了我们的窃窃私语,便回头瞅了我一眼,我们目光短暂交接,然后双方都不无尴尬地埋头吃饭,不说话了。不到十分钟,我丢下被我消灭干净的饭盘子,一溜烟地冲回画室继续画上午未完成的色彩。
在休息时间奋战在画室内的人主要是吴杰、小玉一系列的人。他们对光明前途的执著追求的精神往往能带动整个画室昂扬的气势。这和老张的教法也有莫大的关系。他的特性就是以十分戏谐却又极度残忍的口气将你呕心沥血整整一天才完成的还自以为是的“大作”给批得个“体无完肤”——当然,客观上说,这些画作的水准都是有一点“当当”的。小玉就曾是一个范例。一次,老张在在小玉身边站了多久,又冷又伤人的批评声就持续了多久。我们都不做声,小玉终于忍不住眼泪渗了出来,但是老张没有丝毫欲罢的意思。老张说她混了色,说她昏的光,说她拘谨了笔触,总之就是丢了自己是个该有的样子。话说完后,老张头也不回,走了。鼻子红舯的小玉在自己的画前端详了很久,然后收了那画,又拿出一张白纸,中午她没吃饭,画至晚上十二点过。老张回画室时把这画瞧了又瞧,终于笑了,说:“恩,不错。”小玉笑了,我们都笑了。仿佛有明晃晃的光把朦胧的东西给照明晰了。我们晚上画至两点才睡,早上八点半准时上课,于是八点二十八我们便在手机刺耳的铃声中惊醒,然后胡乱的笼上衣裤便边扣扣子边梳头——那叫一种景致——不吃饭不刷牙(往往是在第一节休息时间再继续这些工序)狂奔至画室再搂着画板努力抻开惺忪睡眼目测一下模特的脸有多宽头发有多长。画至高潮处,只有“刷刷”的铅笔声作响,此时便有“咕咕”的声音此起彼伏而连绵不绝。是的,我们都很饿。饿着肚子依旧一笔一划地勾勒黑白灰,我们都希望个人的手头工夫一天比一天强。十二月,北京的冬天冷得太彻底了,晚上的天地更是冷气怆然。我穿着我的深红色袄子一个人在宽阔的柏油公路上走。每周六晚上画室的人总会异常积极地向我递钞票,原因是让我一个人冒着冷冽寒风步行到遥远的影象店租碟。各个都是老奸巨滑的人精儿了。他们如此推就我是有原因的。很早的一次,我租了陈凯歌的《想和你在一起》和一部老外热情推荐的好莱坞商业大片——其实后者我是不忍心拒绝人家的好意才租的,看之前这一群新青年都排斥乡巴佬似的国产片,看之后大家便异口同声地赞陈导和我了。之后我便成了百姓拥护的这个角了。我兜里揣了于博给的二十块,正在完成我的“光荣”任务。夜晚的这条雄气的路更冷清了,稀拉的汽笛声悄怆浸入城市骨髓。公路的右上空是城铁轨道,下方是火车轨道,这么多的方向通向未来,真是一个充满诱惑而诡异的土地。我我对面坐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有二十多年的军龄,刚从北京探亲回来。我们在吃泡面。我把我带来的泡菜递给他,他便很豪爽地接过然后用叉子将其往面桶里扒。热腾腾的水汽和着酸辣的气味弥漫得浓浓。小玉和于博在个一个小娃儿画像,周围便聚拢了几个神色怡然的观众。在我们座前的一个座,一个穿金戴银的老婆婆很洋气地向一个戴眼镜的老大爷神叨她已经游览了多少个城市。整节车厢就属我们这一块最热闹。这列火车从北京开向成都,车上几乎全是四川人,各个都豪放得很。我对面那个男人一眼就看出我是学美术的。他说:“反正不象跳舞的,你身上有这个(美术)的气质。”我表面嬉笑,想想还真是变着戏法说我邋遢。窗外险山峻陵,阳光明晃却依旧雾气溟朦。又到了秦岭。二零零七年三月八号,我在回家的路上。
老张的画室在五道口一座简朴的宿舍楼里,跟全北京数不胜数的画室比起来,这画室的规模可能就算最小的了。这话是老张自己说的。确实,人家101画室那叫一个“大”,一天光请的模特儿就比咱画室的人还多。可牛皮不是吹的,我们是一支精良的可以打硬仗的特种部队,铆足了劲儿干活那阵仗便是练就真工夫的基础。之所以叫干活,因为大凡学这个的人都晓得这原本是不能跟艺术挂多大钩的(犹如高考作文与文学的关系),又之所以拼命,因为大凡学这个的人都晓得考上心目中那所学校不是光靠运气就可以完事的。我们都是要雄赳赳、气昂昂地挺过鸭绿江的。
我们画室离清华大学太近了。我去“SevenEleven "买泡面时一不小心抬头便远远回收了那座四平八稳建筑的影象。中午我在“重庆小吃”吃鱼香肉丝饭时,老板用重庆话对我说:“那个小伙子也是清华的。在这座楼里打工。”老板用手指了指我身后的那座煞是金碧辉煌的银谷大厦。小伙子似乎是听到了我们的窃窃私语,便回头瞅了我一眼,我们目光短暂交接,然后双方都不无尴尬地埋头吃饭,不说话了。不到十分钟,我丢下被我消灭干净的饭盘子,一溜烟地冲回画室继续画上午未完成的色彩。
在休息时间奋战在画室内的人主要是吴杰、小玉一系列的人。他们对光明前途的执著追求的精神往往能带动整个画室昂扬的气势。这和老张的教法也有莫大的关系。他的特性就是以十分戏谐却又极度残忍的口气将你呕心沥血整整一天才完成的还自以为是的“大作”给批得个“体无完肤”——当然,客观上说,这些画作的水准都是有一点“当当”的。小玉就曾是一个范例。一次,老张在在小玉身边站了多久,又冷又伤人的批评声就持续了多久。我们都不做声,小玉终于忍不住眼泪渗了出来,但是老张没有丝毫欲罢的意思。老张说她混了色,说她昏的光,说她拘谨了笔触,总之就是丢了自己是个该有的样子。话说完后,老张头也不回,走了。鼻子红舯的小玉在自己的画前端详了很久,然后收了那画,又拿出一张白纸,中午她没吃饭,画至晚上十二点过。老张回画室时把这画瞧了又瞧,终于笑了,说:“恩,不错。”小玉笑了,我们都笑了。仿佛有明晃晃的光把朦胧的东西给照明晰了。我们晚上画至两点才睡,早上八点半准时上课,于是八点二十八我们便在手机刺耳的铃声中惊醒,然后胡乱的笼上衣裤便边扣扣子边梳头——那叫一种景致——不吃饭不刷牙(往往是在第一节休息时间再继续这些工序)狂奔至画室再搂着画板努力抻开惺忪睡眼目测一下模特的脸有多宽头发有多长。画至高潮处,只有“刷刷”的铅笔声作响,此时便有“咕咕”的声音此起彼伏而连绵不绝。是的,我们都很饿。饿着肚子依旧一笔一划地勾勒黑白灰,我们都希望个人的手头工夫一天比一天强。十二月,北京的冬天冷得太彻底了,晚上的天地更是冷气怆然。我穿着我的深红色袄子一个人在宽阔的柏油公路上走。每周六晚上画室的人总会异常积极地向我递钞票,原因是让我一个人冒着冷冽寒风步行到遥远的影象店租碟。各个都是老奸巨滑的人精儿了。他们如此推就我是有原因的。很早的一次,我租了陈凯歌的《想和你在一起》和一部老外热情推荐的好莱坞商业大片——其实后者我是不忍心拒绝人家的好意才租的,看之前这一群新青年都排斥乡巴佬似的国产片,看之后大家便异口同声地赞陈导和我了。之后我便成了百姓拥护的这个角了。我兜里揣了于博给的二十块,正在完成我的“光荣”任务。夜晚的这条雄气的路更冷清了,稀拉的汽笛声悄怆浸入城市骨髓。公路的右上空是城铁轨道,下方是火车轨道,这么多的方向通向未来,真是一个充满诱惑而诡异的土地。我我对面坐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有二十多年的军龄,刚从北京探亲回来。我们在吃泡面。我把我带来的泡菜递给他,他便很豪爽地接过然后用叉子将其往面桶里扒。热腾腾的水汽和着酸辣的气味弥漫得浓浓。小玉和于博在个一个小娃儿画像,周围便聚拢了几个神色怡然的观众。在我们座前的一个座,一个穿金戴银的老婆婆很洋气地向一个戴眼镜的老大爷神叨她已经游览了多少个城市。整节车厢就属我们这一块最热闹。这列火车从北京开向成都,车上几乎全是四川人,各个都豪放得很。我对面那个男人一眼就看出我是学美术的。他说:“反正不象跳舞的,你身上有这个(美术)的气质。”我表面嬉笑,想想还真是变着戏法说我邋遢。窗外险山峻陵,阳光明晃却依旧雾气溟朦。又到了秦岭。二零零七年三月八号,我在回家的路上。
老张的画室在五道口一座简朴的宿舍楼里,跟全北京数不胜数的画室比起来,这画室的规模可能就算最小的了。这话是老张自己说的。确实,人家101画室那叫一个“大”,一天光请的模特儿就比咱画室的人还多。可牛皮不是吹的,我们是一支精良的可以打硬仗的特种部队,铆足了劲儿干活那阵仗便是练就真工夫的基础。之所以叫干活,因为大凡学这个的人都晓得这原本是不能跟艺术挂多大钩的(犹如高考作文与文学的关系),又之所以拼命,因为大凡学这个的人都晓得考上心目中那所学校不是光靠运气就可以完事的。我们都是要雄赳赳、气昂昂地挺过鸭绿江的。
我们画室离清华大学太近了。我去“SevenEleven "买泡面时一不小心抬头便远远回收了那座四平八稳建筑的影象。中午我在“重庆小吃”吃鱼香肉丝饭时,老板用重庆话对我说:“那个小伙子也是清华的。在这座楼里打工。”老板用手指了指我身后的那座煞是金碧辉煌的银谷大厦。小伙子似乎是听到了我们的窃窃私语,便回头瞅了我一眼,我们目光短暂交接,然后双方都不无尴尬地埋头吃饭,不说话了。不到十分钟,我丢下被我消灭干净的饭盘子,一溜烟地冲回画室继续画上午未完成的色彩。
在休息时间奋战在画室内的人主要是吴杰、小玉一系列的人。他们对光明前途的执著追求的精神往往能带动整个画室昂扬的气势。这和老张的教法也有莫大的关系。他的特性就是以十分戏谐却又极度残忍的口气将你呕心沥血整整一天才完成的还自以为是的“大作”给批得个“体无完肤”——当然,客观上说,这些画作的水准都是有一点“当当”的。小玉就曾是一个范例。一次,老张在在小玉身边站了多久,又冷又伤人的批评声就持续了多久。我们都不做声,小玉终于忍不住眼泪渗了出来,但是老张没有丝毫欲罢的意思。老张说她混了色,说她昏的光,说她拘谨了笔触,总之就是丢了自己是个该有的样子。话说完后,老张头也不回,走了。鼻子红舯的小玉在自己的画前端详了很久,然后收了那画,又拿出一张白纸,中午她没吃饭,画至晚上十二点过。老张回画室时把这画瞧了又瞧,终于笑了,说:“恩,不错。”小玉笑了,我们都笑了。仿佛有明晃晃的光把朦胧的东西给照明晰了。我们晚上画至两点才睡,早上八点半准时上课,于是八点二十八我们便在手机刺耳的铃声中惊醒,然后胡乱的笼上衣裤便边扣扣子边梳头——那叫一种景致——不吃饭不刷牙(往往是在第一节休息时间再继续这些工序)狂奔至画室再搂着画板努力抻开惺忪睡眼目测一下模特的脸有多宽头发有多长。画至高潮处,只有“刷刷”的铅笔声作响,此时便有“咕咕”的声音此起彼伏而连绵不绝。是的,我们都很饿。饿着肚子依旧一笔一划地勾勒黑白灰,我们都希望个人的手头工夫一天比一天强。十二月,北京的冬天冷得太彻底了,晚上的天地更是冷气怆然。我穿着我的深红色袄子一个人在宽阔的柏油公路上走。每周六晚上画室的人总会异常积极地向我递钞票,原因是让我一个人冒着冷冽寒风步行到遥远的影象店租碟。各个都是老奸巨滑的人精儿了。他们如此推就我是有原因的。很早的一次,我租了陈凯歌的《想和你在一起》和一部老外热情推荐的好莱坞商业大片——其实后者我是不忍心拒绝人家的好意才租的,看之前这一群新青年都排斥乡巴佬似的国产片,看之后大家便异口同声地赞陈导和我了。之后我便成了百姓拥护的这个角了。我兜里揣了于博给的二十块,正在完成我的“光荣”任务。夜晚的这条雄气的路更冷清了,稀拉的汽笛声悄怆浸入城市骨髓。公路的右上空是城铁轨道,下方是火车轨道,这么多的方向通向未来,真是一个充满诱惑而诡异的土地。我我对面坐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有二十多年的军龄,刚从北京探亲回来。我们在吃泡面。我把我带来的泡菜递给他,他便很豪爽地接过然后用叉子将其往面桶里扒。热腾腾的水汽和着酸辣的气味弥漫得浓浓。小玉和于博在个一个小娃儿画像,周围便聚拢了几个神色怡然的观众。在我们座前的一个座,一个穿金戴银的老婆婆很洋气地向一个戴眼镜的老大爷神叨她已经游览了多少个城市。整节车厢就属我们这一块最热闹。这列火车从北京开向成都,车上几乎全是四川人,各个都豪放得很。我对面那个男人一眼就看出我是学美术的。他说:“反正不象跳舞的,你身上有这个(美术)的气质。”我表面嬉笑,想想还真是变着戏法说我邋遢。窗外险山峻陵,阳光明晃却依旧雾气溟朦。又到了秦岭。二零零七年三月八号,我在回家的路上。
老张的画室在五道口一座简朴的宿舍楼里,跟全北京数不胜数的画室比起来,这画室的规模可能就算最小的了。这话是老张自己说的。确实,人家101画室那叫一个“大”,一天光请的模特儿就比咱画室的人还多。可牛皮不是吹的,我们是一支精良的可以打硬仗的特种部队,铆足了劲儿干活那阵仗便是练就真工夫的基础。之所以叫干活,因为大凡学这个的人都晓得这原本是不能跟艺术挂多大钩的(犹如高考作文与文学的关系),又之所以拼命,因为大凡学这个的人都晓得考上心目中那所学校不是光靠运气就可以完事的。我们都是要雄赳赳、气昂昂地挺过鸭绿江的。
我们画室离清华大学太近了。我去“SevenEleven "买泡面时一不小心抬头便远远回收了那座四平八稳建筑的影象。中午我在“重庆小吃”吃鱼香肉丝饭时,老板用重庆话对我说:“那个小伙子也是清华的。在这座楼里打工。”老板用手指了指我身后的那座煞是金碧辉煌的银谷大厦。小伙子似乎是听到了我们的窃窃私语,便回头瞅了我一眼,我们目光短暂交接,然后双方都不无尴尬地埋头吃饭,不说话了。不到十分钟,我丢下被我消灭干净的饭盘子,一溜烟地冲回画室继续画上午未完成的色彩。
在休息时间奋战在画室内的人主要是吴杰、小玉一系列的人。他们对光明前途的执著追求的精神往往能带动整个画室昂扬的气势。这和老张的教法也有莫大的关系。他的特性就是以十分戏谐却又极度残忍的口气将你呕心沥血整整一天才完成的还自以为是的“大作”给批得个“体无完肤”——当然,客观上说,这些画作的水准都是有一点“当当”的。小玉就曾是一个范例。一次,老张在在小玉身边站了多久,又冷又伤人的批评声就持续了多久。我们都不做声,小玉终于忍不住眼泪渗了出来,但是老张没有丝毫欲罢的意思。老张说她混了色,说她昏的光,说她拘谨了笔触,总之就是丢了自己是个该有的样子。话说完后,老张头也不回,走了。鼻子红舯的小玉在自己的画前端详了很久,然后收了那画,又拿出一张白纸,中午她没吃饭,画至晚上十二点过。老张回画室时把这画瞧了又瞧,终于笑了,说:“恩,不错。”小玉笑了,我们都笑了。仿佛有明晃晃的光把朦胧的东西给照明晰了。我们晚上画至两点才睡,早上八点半准时上课,于是八点二十八我们便在手机刺耳的铃声中惊醒,然后胡乱的笼上衣裤便边扣扣子边梳头——那叫一种景致——不吃饭不刷牙(往往是在第一节休息时间再继续这些工序)狂奔至画室再搂着画板努力抻开惺忪睡眼目测一下模特的脸有多宽头发有多长。画至高潮处,只有“刷刷”的铅笔声作响,此时便有“咕咕”的声音此起彼伏而连绵不绝。是的,我们都很饿。饿着肚子依旧一笔一划地勾勒黑白灰,我们都希望个人的手头工夫一天比一天强。十二月,北京的冬天冷得太彻底了,晚上的天地更是冷气怆然。我穿着我的深红色袄子一个人在宽阔的柏油公路上走。每周六晚上画室的人总会异常积极地向我递钞票,原因是让我一个人冒着冷冽寒风步行到遥远的影象店租碟。各个都是老奸巨滑的人精儿了。他们如此推就我是有原因的。很早的一次,我租了陈凯歌的《想和你在一起》和一部老外热情推荐的好莱坞商业大片——其实后者我是不忍心拒绝人家的好意才租的,看之前这一群新青年都排斥乡巴佬似的国产片,看之后大家便异口同声地赞陈导和我了。之后我便成了百姓拥护的这个角了。我兜里揣了于博给的二十块,正在完成我的“光荣”任务。夜晚的这条雄气的路更冷清了,稀拉的汽笛声悄怆浸入城市骨髓。公路的右上空是城铁轨道,下方是火车轨道,这么多的方向通向未来,真是一个充满诱惑而诡异的土地。我我对面坐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有二十多年的军龄,刚从北京探亲回来。我们在吃泡面。我把我带来的泡菜递给他,他便很豪爽地接过然后用叉子将其往面桶里扒。热腾腾的水汽和着酸辣的气味弥漫得浓浓。小玉和于博在个一个小娃儿画像,周围便聚拢了几个神色怡然的观众。在我们座前的一个座,一个穿金戴银的老婆婆很洋气地向一个戴眼镜的老大爷神叨她已经游览了多少个城市。整节车厢就属我们这一块最热闹。这列火车从北京开向成都,车上几乎全是四川人,各个都豪放得很。我对面那个男人一眼就看出我是学美术的。他说:“反正不象跳舞的,你身上有这个(美术)的气质。”我表面嬉笑,想想还真是变着戏法说我邋遢。窗外险山峻陵,阳光明晃却依旧雾气溟朦。又到了秦岭。二零零七年三月八号,我在回家的路上。
老张的画室在五道口一座简朴的宿舍楼里,跟全北京数不胜数的画室比起来,这画室的规模可能就算最小的了。这话是老张自己说的。确实,人家101画室那叫一个“大”,一天光请的模特儿就比咱画室的人还多。可牛皮不是吹的,我们是一支精良的可以打硬仗的特种部队,铆足了劲儿干活那阵仗便是练就真工夫的基础。之所以叫干活,因为大凡学这个的人都晓得这原本是不能跟艺术挂多大钩的(犹如高考作文与文学的关系),又之所以拼命,因为大凡学这个的人都晓得考上心目中那所学校不是光靠运气就可以完事的。我们都是要雄赳赳、气昂昂地挺过鸭绿江的。
我们画室离清华大学太近了。我去“SevenEleven "买泡面时一不小心抬头便远远回收了那座四平八稳建筑的影象。中午我在“重庆小吃”吃鱼香肉丝饭时,老板用重庆话对我说:“那个小伙子也是清华的。在这座楼里打工。”老板用手指了指我身后的那座煞是金碧辉煌的银谷大厦。小伙子似乎是听到了我们的窃窃私语,便回头瞅了我一眼,我们目光短暂交接,然后双方都不无尴尬地埋头吃饭,不说话了。不到十分钟,我丢下被我消灭干净的饭盘子,一溜烟地冲回画室继续画上午未完成的色彩。
在休息时间奋战在画室内的人主要是吴杰、小玉一系列的人。他们对光明前途的执著追求的精神往往能带动整个画室昂扬的气势。这和老张的教法也有莫大的关系。他的特性就是以十分戏谐却又极度残忍的口气将你呕心沥血整整一天才完成的还自以为是的“大作”给批得个“体无完肤”——当然,客观上说,这些画作的水准都是有一点“当当”的。小玉就曾是一个范例。一次,老张在在小玉身边站了多久,又冷又伤人的批评声就持续了多久。我们都不做声,小玉终于忍不住眼泪渗了出来,但是老张没有丝毫欲罢的意思。老张说她混了色,说她昏的光,说她拘谨了笔触,总之就是丢了自己是个该有的样子。话说完后,老张头也不回,走了。鼻子红舯的小玉在自己的画前端详了很久,然后收了那画,又拿出一张白纸,中午她没吃饭,画至晚上十二点过。老张回画室时把这画瞧了又瞧,终于笑了,说:“恩,不错。”小玉笑了,我们都笑了。仿佛有明晃晃的光把朦胧的东西给照明晰了。我们晚上画至两点才睡,早上八点半准时上课,于是八点二十八我们便在手机刺耳的铃声中惊醒,然后胡乱的笼上衣裤便边扣扣子边梳头——那叫一种景致——不吃饭不刷牙(往往是在第一节休息时间再继续这些工序)狂奔至画室再搂着画板努力抻开惺忪睡眼目测一下模特的脸有多宽头发有多长。画至高潮处,只有“刷刷”的铅笔声作响,此时便有“咕咕”的声音此起彼伏而连绵不绝。是的,我们都很饿。饿着肚子依旧一笔一划地勾勒黑白灰,我们都希望个人的手头工夫一天比一天强。十二月,北京的冬天冷得太彻底了,晚上的天地更是冷气怆然。我穿着我的深红色袄子一个人在宽阔的柏油公路上走。每周六晚上画室的人总会异常积极地向我递钞票,原因是让我一个人冒着冷冽寒风步行到遥远的影象店租碟。各个都是老奸巨滑的人精儿了。他们如此推就我是有原因的。很早的一次,我租了陈凯歌的《想和你在一起》和一部老外热情推荐的好莱坞商业大片——其实后者我是不忍心拒绝人家的好意才租的,看之前这一群新青年都排斥乡巴佬似的国产片,看之后大家便异口同声地赞陈导和我了。之后我便成了百姓拥护的这个角了。我兜里揣了于博给的二十块,正在完成我的“光荣”任务。夜晚的这条雄气的路更冷清了,稀拉的汽笛声悄怆浸入城市骨髓。公路的右上空是城铁轨道,下方是火车轨道,这么多的方向通向未来,真是一个充满诱惑而诡异的土地。我我对面坐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有二十多年的军龄,刚从北京探亲回来。我们在吃泡面。我把我带来的泡菜递给他,他便很豪爽地接过然后用叉子将其往面桶里扒。热腾腾的水汽和着酸辣的气味弥漫得浓浓。小玉和于博在个一个小娃儿画像,周围便聚拢了几个神色怡然的观众。在我们座前的一个座,一个穿金戴银的老婆婆很洋气地向一个戴眼镜的老大爷神叨她已经游览了多少个城市。整节车厢就属我们这一块最热闹。这列火车从北京开向成都,车上几乎全是四川人,各个都豪放得很。我对面那个男人一眼就看出我是学美术的。他说:“反正不象跳舞的,你身上有这个(美术)的气质。”我表面嬉笑,想想还真是变着戏法说我邋遢。窗外险山峻陵,阳光明晃却依旧雾气溟朦。又到了秦岭。二零零七年三月八号,我在回家的路上。
老张的画室在五道口一座简朴的宿舍楼里,跟全北京数不胜数的画室比起来,这画室的规模可能就算最小的了。这话是老张自己说的。确实,人家101画室那叫一个“大”,一天光请的模特儿就比咱画室的人还多。可牛皮不是吹的,我们是一支精良的可以打硬仗的特种部队,铆足了劲儿干活那阵仗便是练就真工夫的基础。之所以叫干活,因为大凡学这个的人都晓得这原本是不能跟艺术挂多大钩的(犹如高考作文与文学的关系),又之所以拼命,因为大凡学这个的人都晓得考上心目中那所学校不是光靠运气就可以完事的。我们都是要雄赳赳、气昂昂地挺过鸭绿江的。
我们画室离清华大学太近了。我去“SevenEleven "买泡面时一不小心抬头便远远回收了那座四平八稳建筑的影象。中午我在“重庆小吃”吃鱼香肉丝饭时,老板用重庆话对我说:“那个小伙子也是清华的。在这座楼里打工。”老板用手指了指我身后的那座煞是金碧辉煌的银谷大厦。小伙子似乎是听到了我们的窃窃私语,便回头瞅了我一眼,我们目光短暂交接,然后双方都不无尴尬地埋头吃饭,不说话了。不到十分钟,我丢下被我消灭干净的饭盘子,一溜烟地冲回画室继续画上午未完成的色彩。
在休息时间奋战在画室内的人主要是吴杰、小玉一系列的人。他们对光明前途的执著追求的精神往往能带动整个画室昂扬的气势。这和老张的教法也有莫大的关系。他的特性就是以十分戏谐却又极度残忍的口气将你呕心沥血整整一天才完成的还自以为是的“大作”给批得个“体无完肤”——当然,客观上说,这些画作的水准都是有一点“当当”的。小玉就曾是一个范例。一次,老张在在小玉身边站了多久,又冷又伤人的批评声就持续了多久。我们都不做声,小玉终于忍不住眼泪渗了出来,但是老张没有丝毫欲罢的意思。老张说她混了色,说她昏的光,说她拘谨了笔触,总之就是丢了自己是个该有的样子。话说完后,老张头也不回,走了。鼻子红舯的小玉在自己的画前端详了很久,然后收了那画,又拿出一张白纸,中午她没吃饭,画至晚上十二点过。老张回画室时把这画瞧了又瞧,终于笑了,说:“恩,不错。”小玉笑了,我们都笑了。仿佛有明晃晃的光把朦胧的东西给照明晰了。我们晚上画至两点才睡,早上八点半准时上课,于是八点二十八我们便在手机刺耳的铃声中惊醒,然后胡乱的笼上衣裤便边扣扣子边梳头——那叫一种景致——不吃饭不刷牙(往往是在第一节休息时间再继续这些工序)狂奔至画室再搂着画板努力抻开惺忪睡眼目测一下模特的脸有多宽头发有多长。画至高潮处,只有“刷刷”的铅笔声作响,此时便有“咕咕”的声音此起彼伏而连绵不绝。是的,我们都很饿。饿着肚子依旧一笔一划地勾勒黑白灰,我们都希望个人的手头工夫一天比一天强。十二月,北京的冬天冷得太彻底了,晚上的天地更是冷气怆然。我穿着我的深红色袄子一个人在宽阔的柏油公路上走。每周六晚上画室的人总会异常积极地向我递钞票,原因是让我一个人冒着冷冽寒风步行到遥远的影象店租碟。各个都是老奸巨滑的人精儿了。他们如此推就我是有原因的。很早的一次,我租了陈凯歌的《想和你在一起》和一部老外热情推荐的好莱坞商业大片——其实后者我是不忍心拒绝人家的好意才租的,看之前这一群新青年都排斥乡巴佬似的国产片,看之后大家便异口同声地赞陈导和我了。之后我便成了百姓拥护的这个角了。我兜里揣了于博给的二十块,正在完成我的“光荣”任务。夜晚的这条雄气的路更冷清了,稀拉的汽笛声悄怆浸入城市骨髓。公路的右上空是城铁轨道,下方是火车轨道,这么多的方向通向未来,真是一个充满诱惑而诡异的土地。我我对面坐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有二十多年的军龄,刚从北京探亲回来。我们在吃泡面。我把我带来的泡菜递给他,他便很豪爽地接过然后用叉子将其往面桶里扒。热腾腾的水汽和着酸辣的气味弥漫得浓浓。小玉和于博在个一个小娃儿画像,周围便聚拢了几个神色怡然的观众。在我们座前的一个座,一个穿金戴银的老婆婆很洋气地向一个戴眼镜的老大爷神叨她已经游览了多少个城市。整节车厢就属我们这一块最热闹。这列火车从北京开向成都,车上几乎全是四川人,各个都豪放得很。我对面那个男人一眼就看出我是学美术的。他说:“反正不象跳舞的,你身上有这个(美术)的气质。”我表面嬉笑,想想还真是变着戏法说我邋遢。窗外险山峻陵,阳光明晃却依旧雾气溟朦。又到了秦岭。二零零七年三月八号,我在回家的路上。
老张的画室在五道口一座简朴的宿舍楼里,跟全北京数不胜数的画室比起来,这画室的规模可能就算最小的了。这话是老张自己说的。确实,人家101画室那叫一个“大”,一天光请的模特儿就比咱画室的人还多。可牛皮不是吹的,我们是一支精良的可以打硬仗的特种部队,铆足了劲儿干活那阵仗便是练就真工夫的基础。之所以叫干活,因为大凡学这个的人都晓得这原本是不能跟艺术挂多大钩的(犹如高考作文与文学的关系),又之所以拼命,因为大凡学这个的人都晓得考上心目中那所学校不是光靠运气就可以完事的。我们都是要雄赳赳、气昂昂地挺过鸭绿江的。
我们画室离清华大学太近了。我去“SevenEleven "买泡面时一不小心抬头便远远回收了那座四平八稳建筑的影象。中午我在“重庆小吃”吃鱼香肉丝饭时,老板用重庆话对我说:“那个小伙子也是清华的。在这座楼里打工。”老板用手指了指我身后的那座煞是金碧辉煌的银谷大厦。小伙子似乎是听到了我们的窃窃私语,便回头瞅了我一眼,我们目光短暂交接,然后双方都不无尴尬地埋头吃饭,不说话了。不到十分钟,我丢下被我消灭干净的饭盘子,一溜烟地冲回画室继续画上午未完成的色彩。
在休息时间奋战在画室内的人主要是吴杰、小玉一系列的人。他们对光明前途的执著追求的精神往往能带动整个画室昂扬的气势。这和老张的教法也有莫大的关系。他的特性就是以十分戏谐却又极度残忍的口气将你呕心沥血整整一天才完成的还自以为是的“大作”给批得个“体无完肤”——当然,客观上说,这些画作的水准都是有一点“当当”的。小玉就曾是一个范例。一次,老张在在小玉身边站了多久,又冷又伤人的批评声就持续了多久。我们都不做声,小玉终于忍不住眼泪渗了出来,但是老张没有丝毫欲罢的意思。老张说她混了色,说她昏的光,说她拘谨了笔触,总之就是丢了自己是个该有的样子。话说完后,老张头也不回,走了。鼻子红舯的小玉在自己的画前端详了很久,然后收了那画,又拿出一张白纸,中午她没吃饭,画至晚上十二点过。老张回画室时把这画瞧了又瞧,终于笑了,说:“恩,不错。”小玉笑了,我们都笑了。仿佛有明晃晃的光把朦胧的东西给照明晰了。我们晚上画至两点才睡,早上八点半准时上课,于是八点二十八我们便在手机刺耳的铃声中惊醒,然后胡乱的笼上衣裤便边扣扣子边梳头——那叫一种景致——不吃饭不刷牙(往往是在第一节休息时间再继续这些工序)狂奔至画室再搂着画板努力抻开惺忪睡眼目测一下模特的脸有多宽头发有多长。画至高潮处,只有“刷刷”的铅笔声作响,此时便有“咕咕”的声音此起彼伏而连绵不绝。是的,我们都很饿。饿着肚子依旧一笔一划地勾勒黑白灰,我们都希望个人的手头工夫一天比一天强。十二月,北京的冬天冷得太彻底了,晚上的天地更是冷气怆然。我穿着我的深红色袄子一个人在宽阔的柏油公路上走。每周六晚上画室的人总会异常积极地向我递钞票,原因是让我一个人冒着冷冽寒风步行到遥远的影象店租碟。各个都是老奸巨滑的人精儿了。他们如此推就我是有原因的。很早的一次,我租了陈凯歌的《想和你在一起》和一部老外热情推荐的好莱坞商业大片——其实后者我是不忍心拒绝人家的好意才租的,看之前这一群新青年都排斥乡巴佬似的国产片,看之后大家便异口同声地赞陈导和我了。之后我便成了百姓拥护的这个角了。我兜里揣了于博给的二十块,正在完成我的“光荣”任务。夜晚的这条雄气的路更冷清了,稀拉的汽笛声悄怆浸入城市骨髓。公路的右上空是城铁轨道,下方是火车轨道,这么多的方向通向未来,真是一个充满诱惑而诡异的土地。我

好文章,赞一下
612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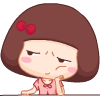
很一般,需努力
7712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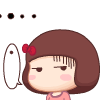
太差劲,踩一下
101人
- 上一篇:假如作文300字
- 下一篇:当李商隐遇上柳枝作文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