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欠秋天 9500字
文章摘要:高三写景作文:怎么写好只欠秋天9500字作文?他倚在天桥最顶端的扶手边,然后缓缓地张开双臂,向后一点点倾斜。下面是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嗡嗡嘀嘀的鸣笛声,我的耳膜不可抑止地颤动,那些恐慌顺着我的听觉神经传到大脑,形成一片颠覆的回声。那张俊秀的脸上极尽苍白,在它一点点沉陷下去时我尖着嗓子喊了一声,你要掉下去了。以下是叶冬珥写的《只欠秋天》范文;
好只欠秋天作文9500字概况
- 作者:叶冬珥
- 班级:高中高三
- 字数:9500字作文
- 体裁:写景
- 段落:分105段叙写
- 更新:2021年11月12日 04时02分
他倚在天桥最顶端的扶手边,然后缓缓地张开双臂,向后一点点倾斜。
下面是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嗡嗡嘀嘀的鸣笛声,我的耳膜不可抑止地颤动,那些恐慌顺着我的听觉神经传到大脑,形成一片颠覆的回声。那张俊秀的脸上极尽苍白,在它一点点沉陷下去时我尖着嗓子喊了一声,你要掉下去了!他直起身子,似笑非笑地说,你知道么?人的灵魂往往被禁锢在载体上,因而它们无法得到自由——载体消失了,灵魂也就被放逐了。我睖睁着眼睛,他说我们走吧。嗯。
每个清晨六点一刻,我都会很准时地站在离家两百米的站牌下等公车。
在那个冬天我喜欢围一条粉蓝色的围巾,然后手里捧着母亲温好的500mL牛奶。公车有时会来得很仓促,它乍亮的车灯会使还未来得及从暖色调恢复过来的我的视觉神经猛地一痛,然后我摸索着口袋里早已备好的一元硬币,“哐啷!”。我习惯性地向后座走去,天已泛起鱼肚白的颜色,阳光浮在车窗上不肯探进头来。车厢里的温度是在不怎么高,我喝了口热牛奶,吐出的白气像极了儿时稀薄的记忆,我有些兴奋地用手指在其中比划。一阵细微的鼾声把我惊醒,四下张望,才发现最里排最后座有一个倚着窗框的人。他手里捧着一杯热可可,上面氤氲着依稀可见的一小团白雾。他的背包懒散地躺在他身边,没有拉紧的拉链里隐隐浮现出“新概念”的字样。公车突然一个急转弯,他的头被磕到窗框上。他抬头看到了我审视的目光,微微一笑,便整好自己的东西准备下车。
公车内鸣了到站铃,他不客气地首先走了出去,我背着书包径直走下去将牛奶盒丢到了垃圾箱里。到学校后,他走在我前面,两人相隔5米。楼梯转角,他突然转过头来,冷秋,再见咯!冷秋。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
初一时我结识了一个名叫聂双的笔友,直到初三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他告诉我他的本名是聂子双,因为自己讨厌“子”所以将“子”去掉了。他是个温暖又很忧伤的男孩子,他的行书异常飘逸却总携着孤独和忧愁的味道。我记得有一次他寄来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字迹很凌乱,我被他的第一句话吓到了,他说,冷秋,帮我!我不知道自己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完那些被遗弃被孤立的数万字,他反复强调“双子座的人宿命就是游离和破碎”,他说“一个爱文字甚于爱生命的人无法写出真实的表达”使他异常痛苦……我的心在那么一瞬被一股强大的力给击溃,我咬着牙却道不出那种分离游离的痛苦。“聂双,我们是朋友……你永远的朋友,冷秋。”
从那次起他的出现就不再唐突,我们会在见面时彼此会意一笑。阳光总是毫不吝啬地洒落在他的脸上,他极少睁开眼,可一旦睁开,那清澈的眸子又会摄人心魄。
我倚着靠垫享受着阳光的微醺。他真像聂双,有时我会忍不住地这么想。我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我梦到他抚着我的头发抑或点点我的额头用着嗔怪的语气和我说话,在阳光的影子里他脸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只剩一个勾着忧伤微笑的嘴角,我伸出手去想要抓住他……“到站了。”我有些惊慌地睁开眼,却发现自己细小的手指头被他轻轻地握着。“哦,对不起……”我迅速抽回手有些慌张地逃似地跑下车。
聂双来信了,上一封信里我对聂双提到了他。聂双说他来这边了,想见我,然后便只剩一串地址:湘斯路天桥(顶端)。我不懂括号里字的意思,可又无从去问。聂双说的时间是在周五,于是我请了两节课的作文自修。
这边的气候比想象中的更加恶劣,呼啸的寒风吹疼了我的脸。我在人行道时就瞥见了天桥上一个羸弱的少年身影,他背对着我。那身影像极了他。恍惚间他们就是一个可合可离的混合体,一样的行为、一样的言语。
秋。他开口喊我的时候我还是无法抑制自己地跌落在地下。原来,我早该猜到。
他嘴边浅浅的微笑让我唐突地产生了错觉,到底聂双是他?还是他是聂双?
他在秋的最后一天出生,生日却被冠上了虚假的双子。所有的真伪就那么变成了虚无,我原以为我是他灵魂深处另一个意识形态的他,此刻才发觉我亦是一个被驱逐至角落的双子。
我其实叫聂文盛。他开口的 只欠秋天他倚在天桥最顶端的扶手边,然后缓缓地张开双臂,向后一点点倾斜。
下面是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嗡嗡嘀嘀的鸣笛声,我的耳膜不可抑止地颤动,那些恐慌顺着我的听觉神经传到大脑,形成一片颠覆的回声。那张俊秀的脸上极尽苍白,在它一点点沉陷下去时我尖着嗓子喊了一声,你要掉下去了!他直起身子,似笑非笑地说,你知道么?人的灵魂往往被禁锢在载体上,因而它们无法得到自由——载体消失了,灵魂也就被放逐了。我睖睁着眼睛,他说我们走吧。嗯。
每个清晨六点一刻,我都会很准时地站在离家两百米的站牌下等公车。
在那个冬天我喜欢围一条粉蓝色的围巾,然后手里捧着母亲温好的500mL牛奶。公车有时会来得很仓促,它乍亮的车灯会使还未来得及从暖色调恢复过来的我的视觉神经猛地一痛,然后我摸索着口袋里早已备好的一元硬币,“哐啷!”。我习惯性地向后座走去,天已泛起鱼肚白的颜色,阳光浮在车窗上不肯探进头来。车厢里的温度是在不怎么高,我喝了口热牛奶,吐出的白气像极了儿时稀薄的记忆,我有些兴奋地用手指在其中比划。一阵细微的鼾声把我惊醒,四下张望,才发现最里排最后座有一个倚着窗框的人。他手里捧着一杯热可可,上面氤氲着依稀可见的一小团白雾。他的背包懒散地躺在他身边,没有拉紧的拉链里隐隐浮现出“新概念”的字样。公车突然一个急转弯,他的头被磕到窗框上。他抬头看到了我审视的目光,微微一笑,便整好自己的东西准备下车。
公车内鸣了到站铃,他不客气地首先走了出去,我背着书包径直走下去将牛奶盒丢到了垃圾箱里。到学校后,他走在我前面,两人相隔5米。楼梯转角,他突然转过头来,冷秋,再见咯!冷秋。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
初一时我结识了一个名叫聂双的笔友,直到初三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他告诉我他的本名是聂子双,因为自己讨厌“子”所以将“子”去掉了。他是个温暖又很忧伤的男孩子,他的行书异常飘逸却总携着孤独和忧愁的味道。我记得有一次他寄来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字迹很凌乱,我被他的第一句话吓到了,他说,冷秋,帮我!我不知道自己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完那些被遗弃被孤立的数万字,他反复强调“双子座的人宿命就是游离和破碎”,他说“一个爱文字甚于爱生命的人无法写出真实的表达”使他异常痛苦……我的心在那么一瞬被一股强大的力给击溃,我咬着牙却道不出那种分离游离的痛苦。“聂双,我们是朋友……你永远的朋友,冷秋。”
从那次起他的出现就不再唐突,我们会在见面时彼此会意一笑。阳光总是毫不吝啬地洒落在他的脸上,他极少睁开眼,可一旦睁开,那清澈的眸子又会摄人心魄。
我倚着靠垫享受着阳光的微醺。他真像聂双,有时我会忍不住地这么想。我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我梦到他抚着我的头发抑或点点我的额头用着嗔怪的语气和我说话,在阳光的影子里他脸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只剩一个勾着忧伤微笑的嘴角,我伸出手去想要抓住他……“到站了。”我有些惊慌地睁开眼,却发现自己细小的手指头被他轻轻地握着。“哦,对不起……”我迅速抽回手有些慌张地逃似地跑下车。
聂双来信了,上一封信里我对聂双提到了他。聂双说他来这边了,想见我,然后便只剩一串地址:湘斯路天桥(顶端)。我不懂括号里字的意思,可又无从去问。聂双说的时间是在周五,于是我请了两节课的作文自修。
这边的气候比想象中的更加恶劣,呼啸的寒风吹疼了我的脸。我在人行道时就瞥见了天桥上一个羸弱的少年身影,他背对着我。那身影像极了他。恍惚间他们就是一个可合可离的混合体,一样的行为、一样的言语。
秋。他开口喊我的时候我还是无法抑制自己地跌落在地下。原来,我早该猜到。
他嘴边浅浅的微笑让我唐突地产生了错觉,到底聂双是他?还是他是聂双?
他在秋的最后一天出生,生日却被冠上了虚假的双子。所有的真伪就那么变成了虚无,我原以为我是他灵魂深处另一个意识形态的他,此刻才发觉我亦是一个被驱逐至角落的双子。
我其实叫聂文盛。他开口的 只欠秋天他倚在天桥最顶端的扶手边,然后缓缓地张开双臂,向后一点点倾斜。
下面是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嗡嗡嘀嘀的鸣笛声,我的耳膜不可抑止地颤动,那些恐慌顺着我的听觉神经传到大脑,形成一片颠覆的回声。那张俊秀的脸上极尽苍白,在它一点点沉陷下去时我尖着嗓子喊了一声,你要掉下去了!他直起身子,似笑非笑地说,你知道么?人的灵魂往往被禁锢在载体上,因而它们无法得到自由——载体消失了,灵魂也就被放逐了。我睖睁着眼睛,他说我们走吧。嗯。
每个清晨六点一刻,我都会很准时地站在离家两百米的站牌下等公车。
在那个冬天我喜欢围一条粉蓝色的围巾,然后手里捧着母亲温好的500mL牛奶。公车有时会来得很仓促,它乍亮的车灯会使还未来得及从暖色调恢复过来的我的视觉神经猛地一痛,然后我摸索着口袋里早已备好的一元硬币,“哐啷!”。我习惯性地向后座走去,天已泛起鱼肚白的颜色,阳光浮在车窗上不肯探进头来。车厢里的温度是在不怎么高,我喝了口热牛奶,吐出的白气像极了儿时稀薄的记忆,我有些兴奋地用手指在其中比划。一阵细微的鼾声把我惊醒,四下张望,才发现最里排最后座有一个倚着窗框的人。他手里捧着一杯热可可,上面氤氲着依稀可见的一小团白雾。他的背包懒散地躺在他身边,没有拉紧的拉链里隐隐浮现出“新概念”的字样。公车突然一个急转弯,他的头被磕到窗框上。他抬头看到了我审视的目光,微微一笑,便整好自己的东西准备下车。
公车内鸣了到站铃,他不客气地首先走了出去,我背着书包径直走下去将牛奶盒丢到了垃圾箱里。到学校后,他走在我前面,两人相隔5米。楼梯转角,他突然转过头来,冷秋,再见咯!冷秋。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
初一时我结识了一个名叫聂双的笔友,直到初三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他告诉我他的本名是聂子双,因为自己讨厌“子”所以将“子”去掉了。他是个温暖又很忧伤的男孩子,他的行书异常飘逸却总携着孤独和忧愁的味道。我记得有一次他寄来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字迹很凌乱,我被他的第一句话吓到了,他说,冷秋,帮我!我不知道自己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完那些被遗弃被孤立的数万字,他反复强调“双子座的人宿命就是游离和破碎”,他说“一个爱文字甚于爱生命的人无法写出真实的表达”使他异常痛苦……我的心在那么一瞬被一股强大的力给击溃,我咬着牙却道不出那种分离游离的痛苦。“聂双,我们是朋友……你永远的朋友,冷秋。”
从那次起他的出现就不再唐突,我们会在见面时彼此会意一笑。阳光总是毫不吝啬地洒落在他的脸上,他极少睁开眼,可一旦睁开,那清澈的眸子又会摄人心魄。
我倚着靠垫享受着阳光的微醺。他真像聂双,有时我会忍不住地这么想。我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我梦到他抚着我的头发抑或点点我的额头用着嗔怪的语气和我说话,在阳光的影子里他脸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只剩一个勾着忧伤微笑的嘴角,我伸出手去想要抓住他……“到站了。”我有些惊慌地睁开眼,却发现自己细小的手指头被他轻轻地握着。“哦,对不起……”我迅速抽回手有些慌张地逃似地跑下车。
聂双来信了,上一封信里我对聂双提到了他。聂双说他来这边了,想见我,然后便只剩一串地址:湘斯路天桥(顶端)。我不懂括号里字的意思,可又无从去问。聂双说的时间是在周五,于是我请了两节课的作文自修。
这边的气候比想象中的更加恶劣,呼啸的寒风吹疼了我的脸。我在人行道时就瞥见了天桥上一个羸弱的少年身影,他背对着我。那身影像极了他。恍惚间他们就是一个可合可离的混合体,一样的行为、一样的言语。
秋。他开口喊我的时候我还是无法抑制自己地跌落在地下。原来,我早该猜到。
他嘴边浅浅的微笑让我唐突地产生了错觉,到底聂双是他?还是他是聂双?
他在秋的最后一天出生,生日却被冠上了虚假的双子。所有的真伪就那么变成了虚无,我原以为我是他灵魂深处另一个意识形态的他,此刻才发觉我亦是一个被驱逐至角落的双子。
我其实叫聂文盛。他开口的 只欠秋天他倚在天桥最顶端的扶手边,然后缓缓地张开双臂,向后一点点倾斜。
下面是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嗡嗡嘀嘀的鸣笛声,我的耳膜不可抑止地颤动,那些恐慌顺着我的听觉神经传到大脑,形成一片颠覆的回声。那张俊秀的脸上极尽苍白,在它一点点沉陷下去时我尖着嗓子喊了一声,你要掉下去了!他直起身子,似笑非笑地说,你知道么?人的灵魂往往被禁锢在载体上,因而它们无法得到自由——载体消失了,灵魂也就被放逐了。我睖睁着眼睛,他说我们走吧。嗯。
每个清晨六点一刻,我都会很准时地站在离家两百米的站牌下等公车。
在那个冬天我喜欢围一条粉蓝色的围巾,然后手里捧着母亲温好的500mL牛奶。公车有时会来得很仓促,它乍亮的车灯会使还未来得及从暖色调恢复过来的我的视觉神经猛地一痛,然后我摸索着口袋里早已备好的一元硬币,“哐啷!”。我习惯性地向后座走去,天已泛起鱼肚白的颜色,阳光浮在车窗上不肯探进头来。车厢里的温度是在不怎么高,我喝了口热牛奶,吐出的白气像极了儿时稀薄的记忆,我有些兴奋地用手指在其中比划。一阵细微的鼾声把我惊醒,四下张望,才发现最里排最后座有一个倚着窗框的人。他手里捧着一杯热可可,上面氤氲着依稀可见的一小团白雾。他的背包懒散地躺在他身边,没有拉紧的拉链里隐隐浮现出“新概念”的字样。公车突然一个急转弯,他的头被磕到窗框上。他抬头看到了我审视的目光,微微一笑,便整好自己的东西准备下车。
公车内鸣了到站铃,他不客气地首先走了出去,我背着书包径直走下去将牛奶盒丢到了垃圾箱里。到学校后,他走在我前面,两人相隔5米。楼梯转角,他突然转过头来,冷秋,再见咯!冷秋。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
初一时我结识了一个名叫聂双的笔友,直到初三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他告诉我他的本名是聂子双,因为自己讨厌“子”所以将“子”去掉了。他是个温暖又很忧伤的男孩子,他的行书异常飘逸却总携着孤独和忧愁的味道。我记得有一次他寄来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字迹很凌乱,我被他的第一句话吓到了,他说,冷秋,帮我!我不知道自己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完那些被遗弃被孤立的数万字,他反复强调“双子座的人宿命就是游离和破碎”,他说“一个爱文字甚于爱生命的人无法写出真实的表达”使他异常痛苦……我的心在那么一瞬被一股强大的力给击溃,我咬着牙却道不出那种分离游离的痛苦。“聂双,我们是朋友……你永远的朋友,冷秋。”
从那次起他的出现就不再唐突,我们会在见面时彼此会意一笑。阳光总是毫不吝啬地洒落在他的脸上,他极少睁开眼,可一旦睁开,那清澈的眸子又会摄人心魄。
我倚着靠垫享受着阳光的微醺。他真像聂双,有时我会忍不住地这么想。我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我梦到他抚着我的头发抑或点点我的额头用着嗔怪的语气和我说话,在阳光的影子里他脸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只剩一个勾着忧伤微笑的嘴角,我伸出手去想要抓住他……“到站了。”我有些惊慌地睁开眼,却发现自己细小的手指头被他轻轻地握着。“哦,对不起……”我迅速抽回手有些慌张地逃似地跑下车。
聂双来信了,上一封信里我对聂双提到了他。聂双说他来这边了,想见我,然后便只剩一串地址:湘斯路天桥(顶端)。我不懂括号里字的意思,可又无从去问。聂双说的时间是在周五,于是我请了两节课的作文自修。
这边的气候比想象中的更加恶劣,呼啸的寒风吹疼了我的脸。我在人行道时就瞥见了天桥上一个羸弱的少年身影,他背对着我。那身影像极了他。恍惚间他们就是一个可合可离的混合体,一样的行为、一样的言语。
秋。他开口喊我的时候我还是无法抑制自己地跌落在地下。原来,我早该猜到。
他嘴边浅浅的微笑让我唐突地产生了错觉,到底聂双是他?还是他是聂双?
他在秋的最后一天出生,生日却被冠上了虚假的双子。所有的真伪就那么变成了虚无,我原以为我是他灵魂深处另一个意识形态的他,此刻才发觉我亦是一个被驱逐至角落的双子。
我其实叫聂文盛。他开口的 只欠秋天他倚在天桥最顶端的扶手边,然后缓缓地张开双臂,向后一点点倾斜。
下面是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嗡嗡嘀嘀的鸣笛声,我的耳膜不可抑止地颤动,那些恐慌顺着我的听觉神经传到大脑,形成一片颠覆的回声。那张俊秀的脸上极尽苍白,在它一点点沉陷下去时我尖着嗓子喊了一声,你要掉下去了!他直起身子,似笑非笑地说,你知道么?人的灵魂往往被禁锢在载体上,因而它们无法得到自由——载体消失了,灵魂也就被放逐了。我睖睁着眼睛,他说我们走吧。嗯。
每个清晨六点一刻,我都会很准时地站在离家两百米的站牌下等公车。
在那个冬天我喜欢围一条粉蓝色的围巾,然后手里捧着母亲温好的500mL牛奶。公车有时会来得很仓促,它乍亮的车灯会使还未来得及从暖色调恢复过来的我的视觉神经猛地一痛,然后我摸索着口袋里早已备好的一元硬币,“哐啷!”。我习惯性地向后座走去,天已泛起鱼肚白的颜色,阳光浮在车窗上不肯探进头来。车厢里的温度是在不怎么高,我喝了口热牛奶,吐出的白气像极了儿时稀薄的记忆,我有些兴奋地用手指在其中比划。一阵细微的鼾声把我惊醒,四下张望,才发现最里排最后座有一个倚着窗框的人。他手里捧着一杯热可可,上面氤氲着依稀可见的一小团白雾。他的背包懒散地躺在他身边,没有拉紧的拉链里隐隐浮现出“新概念”的字样。公车突然一个急转弯,他的头被磕到窗框上。他抬头看到了我审视的目光,微微一笑,便整好自己的东西准备下车。
公车内鸣了到站铃,他不客气地首先走了出去,我背着书包径直走下去将牛奶盒丢到了垃圾箱里。到学校后,他走在我前面,两人相隔5米。楼梯转角,他突然转过头来,冷秋,再见咯!冷秋。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
初一时我结识了一个名叫聂双的笔友,直到初三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他告诉我他的本名是聂子双,因为自己讨厌“子”所以将“子”去掉了。他是个温暖又很忧伤的男孩子,他的行书异常飘逸却总携着孤独和忧愁的味道。我记得有一次他寄来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字迹很凌乱,我被他的第一句话吓到了,他说,冷秋,帮我!我不知道自己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完那些被遗弃被孤立的数万字,他反复强调“双子座的人宿命就是游离和破碎”,他说“一个爱文字甚于爱生命的人无法写出真实的表达”使他异常痛苦……我的心在那么一瞬被一股强大的力给击溃,我咬着牙却道不出那种分离游离的痛苦。“聂双,我们是朋友……你永远的朋友,冷秋。”
从那次起他的出现就不再唐突,我们会在见面时彼此会意一笑。阳光总是毫不吝啬地洒落在他的脸上,他极少睁开眼,可一旦睁开,那清澈的眸子又会摄人心魄。
我倚着靠垫享受着阳光的微醺。他真像聂双,有时我会忍不住地这么想。我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我梦到他抚着我的头发抑或点点我的额头用着嗔怪的语气和我说话,在阳光的影子里他脸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只剩一个勾着忧伤微笑的嘴角,我伸出手去想要抓住他……“到站了。”我有些惊慌地睁开眼,却发现自己细小的手指头被他轻轻地握着。“哦,对不起……”我迅速抽回手有些慌张地逃似地跑下车。
聂双来信了,上一封信里我对聂双提到了他。聂双说他来这边了,想见我,然后便只剩一串地址:湘斯路天桥(顶端)。我不懂括号里字的意思,可又无从去问。聂双说的时间是在周五,于是我请了两节课的作文自修。
这边的气候比想象中的更加恶劣,呼啸的寒风吹疼了我的脸。我在人行道时就瞥见了天桥上一个羸弱的少年身影,他背对着我。那身影像极了他。恍惚间他们就是一个可合可离的混合体,一样的行为、一样的言语。
秋。他开口喊我的时候我还是无法抑制自己地跌落在地下。原来,我早该猜到。
他嘴边浅浅的微笑让我唐突地产生了错觉,到底聂双是他?还是他是聂双?
他在秋的最后一天出生,生日却被冠上了虚假的双子。所有的真伪就那么变成了虚无,我原以为我是他灵魂深处另一个意识形态的他,此刻才发觉我亦是一个被驱逐至角落的双子。
我其实叫聂文盛。他开口的 只欠秋天他倚在天桥最顶端的扶手边,然后缓缓地张开双臂,向后一点点倾斜。
下面是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嗡嗡嘀嘀的鸣笛声,我的耳膜不可抑止地颤动,那些恐慌顺着我的听觉神经传到大脑,形成一片颠覆的回声。那张俊秀的脸上极尽苍白,在它一点点沉陷下去时我尖着嗓子喊了一声,你要掉下去了!他直起身子,似笑非笑地说,你知道么?人的灵魂往往被禁锢在载体上,因而它们无法得到自由——载体消失了,灵魂也就被放逐了。我睖睁着眼睛,他说我们走吧。嗯。
每个清晨六点一刻,我都会很准时地站在离家两百米的站牌下等公车。
在那个冬天我喜欢围一条粉蓝色的围巾,然后手里捧着母亲温好的500mL牛奶。公车有时会来得很仓促,它乍亮的车灯会使还未来得及从暖色调恢复过来的我的视觉神经猛地一痛,然后我摸索着口袋里早已备好的一元硬币,“哐啷!”。我习惯性地向后座走去,天已泛起鱼肚白的颜色,阳光浮在车窗上不肯探进头来。车厢里的温度是在不怎么高,我喝了口热牛奶,吐出的白气像极了儿时稀薄的记忆,我有些兴奋地用手指在其中比划。一阵细微的鼾声把我惊醒,四下张望,才发现最里排最后座有一个倚着窗框的人。他手里捧着一杯热可可,上面氤氲着依稀可见的一小团白雾。他的背包懒散地躺在他身边,没有拉紧的拉链里隐隐浮现出“新概念”的字样。公车突然一个急转弯,他的头被磕到窗框上。他抬头看到了我审视的目光,微微一笑,便整好自己的东西准备下车。
公车内鸣了到站铃,他不客气地首先走了出去,我背着书包径直走下去将牛奶盒丢到了垃圾箱里。到学校后,他走在我前面,两人相隔5米。楼梯转角,他突然转过头来,冷秋,再见咯!冷秋。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
初一时我结识了一个名叫聂双的笔友,直到初三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他告诉我他的本名是聂子双,因为自己讨厌“子”所以将“子”去掉了。他是个温暖又很忧伤的男孩子,他的行书异常飘逸却总携着孤独和忧愁的味道。我记得有一次他寄来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字迹很凌乱,我被他的第一句话吓到了,他说,冷秋,帮我!我不知道自己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完那些被遗弃被孤立的数万字,他反复强调“双子座的人宿命就是游离和破碎”,他说“一个爱文字甚于爱生命的人无法写出真实的表达”使他异常痛苦……我的心在那么一瞬被一股强大的力给击溃,我咬着牙却道不出那种分离游离的痛苦。“聂双,我们是朋友……你永远的朋友,冷秋。”
从那次起他的出现就不再唐突,我们会在见面时彼此会意一笑。阳光总是毫不吝啬地洒落在他的脸上,他极少睁开眼,可一旦睁开,那清澈的眸子又会摄人心魄。
我倚着靠垫享受着阳光的微醺。他真像聂双,有时我会忍不住地这么想。我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我梦到他抚着我的头发抑或点点我的额头用着嗔怪的语气和我说话,在阳光的影子里他脸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只剩一个勾着忧伤微笑的嘴角,我伸出手去想要抓住他……“到站了。”我有些惊慌地睁开眼,却发现自己细小的手指头被他轻轻地握着。“哦,对不起……”我迅速抽回手有些慌张地逃似地跑下车。
聂双来信了,上一封信里我对聂双提到了他。聂双说他来这边了,想见我,然后便只剩一串地址:湘斯路天桥(顶端)。我不懂括号里字的意思,可又无从去问。聂双说的时间是在周五,于是我请了两节课的作文自修。
这边的气候比想象中的更加恶劣,呼啸的寒风吹疼了我的脸。我在人行道时就瞥见了天桥上一个羸弱的少年身影,他背对着我。那身影像极了他。恍惚间他们就是一个可合可离的混合体,一样的行为、一样的言语。
秋。他开口喊我的时候我还是无法抑制自己地跌落在地下。原来,我早该猜到。
他嘴边浅浅的微笑让我唐突地产生了错觉,到底聂双是他?还是他是聂双?
他在秋的最后一天出生,生日却被冠上了虚假的双子。所有的真伪就那么变成了虚无,我原以为我是他灵魂深处另一个意识形态的他,此刻才发觉我亦是一个被驱逐至角落的双子。
我其实叫聂文盛。他开口的 只欠秋天他倚在天桥最顶端的扶手边,然后缓缓地张开双臂,向后一点点倾斜。
下面是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嗡嗡嘀嘀的鸣笛声,我的耳膜不可抑止地颤动,那些恐慌顺着我的听觉神经传到大脑,形成一片颠覆的回声。那张俊秀的脸上极尽苍白,在它一点点沉陷下去时我尖着嗓子喊了一声,你要掉下去了!他直起身子,似笑非笑地说,你知道么?人的灵魂往往被禁锢在载体上,因而它们无法得到自由——载体消失了,灵魂也就被放逐了。我睖睁着眼睛,他说我们走吧。嗯。
每个清晨六点一刻,我都会很准时地站在离家两百米的站牌下等公车。
在那个冬天我喜欢围一条粉蓝色的围巾,然后手里捧着母亲温好的500mL牛奶。公车有时会来得很仓促,它乍亮的车灯会使还未来得及从暖色调恢复过来的我的视觉神经猛地一痛,然后我摸索着口袋里早已备好的一元硬币,“哐啷!”。我习惯性地向后座走去,天已泛起鱼肚白的颜色,阳光浮在车窗上不肯探进头来。车厢里的温度是在不怎么高,我喝了口热牛奶,吐出的白气像极了儿时稀薄的记忆,我有些兴奋地用手指在其中比划。一阵细微的鼾声把我惊醒,四下张望,才发现最里排最后座有一个倚着窗框的人。他手里捧着一杯热可可,上面氤氲着依稀可见的一小团白雾。他的背包懒散地躺在他身边,没有拉紧的拉链里隐隐浮现出“新概念”的字样。公车突然一个急转弯,他的头被磕到窗框上。他抬头看到了我审视的目光,微微一笑,便整好自己的东西准备下车。
公车内鸣了到站铃,他不客气地首先走了出去,我背着书包径直走下去将牛奶盒丢到了垃圾箱里。到学校后,他走在我前面,两人相隔5米。楼梯转角,他突然转过头来,冷秋,再见咯!冷秋。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
初一时我结识了一个名叫聂双的笔友,直到初三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他告诉我他的本名是聂子双,因为自己讨厌“子”所以将“子”去掉了。他是个温暖又很忧伤的男孩子,他的行书异常飘逸却总携着孤独和忧愁的味道。我记得有一次他寄来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字迹很凌乱,我被他的第一句话吓到了,他说,冷秋,帮我!我不知道自己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完那些被遗弃被孤立的数万字,他反复强调“双子座的人宿命就是游离和破碎”,他说“一个爱文字甚于爱生命的人无法写出真实的表达”使他异常痛苦……我的心在那么一瞬被一股强大的力给击溃,我咬着牙却道不出那种分离游离的痛苦。“聂双,我们是朋友……你永远的朋友,冷秋。”
从那次起他的出现就不再唐突,我们会在见面时彼此会意一笑。阳光总是毫不吝啬地洒落在他的脸上,他极少睁开眼,可一旦睁开,那清澈的眸子又会摄人心魄。
我倚着靠垫享受着阳光的微醺。他真像聂双,有时我会忍不住地这么想。我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我梦到他抚着我的头发抑或点点我的额头用着嗔怪的语气和我说话,在阳光的影子里他脸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只剩一个勾着忧伤微笑的嘴角,我伸出手去想要抓住他……“到站了。”我有些惊慌地睁开眼,却发现自己细小的手指头被他轻轻地握着。“哦,对不起……”我迅速抽回手有些慌张地逃似地跑下车。
聂双来信了,上一封信里我对聂双提到了他。聂双说他来这边了,想见我,然后便只剩一串地址:湘斯路天桥(顶端)。我不懂括号里字的意思,可又无从去问。聂双说的时间是在周五,于是我请了两节课的作文自修。
这边的气候比想象中的更加恶劣,呼啸的寒风吹疼了我的脸。我在人行道时就瞥见了天桥上一个羸弱的少年身影,他背对着我。那身影像极了他。恍惚间他们就是一个可合可离的混合体,一样的行为、一样的言语。
秋。他开口喊我的时候我还是无法抑制自己地跌落在地下。原来,我早该猜到。
他嘴边浅浅的微笑让我唐突地产生了错觉,到底聂双是他?还是他是聂双?
他在秋的最后一天出生,生日却被冠上了虚假的双子。所有的真伪就那么变成了虚无,我原以为我是他灵魂深处另一个意识形态的他,此刻才发觉我亦是一个被驱逐至角落的双子。
我其实叫聂文盛。他开口的

好文章,赞一下
535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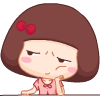
很一般,需努力
7635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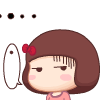
太差劲,踩一下
2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