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 10000字
文章摘要:高三作文10000字:怎么写好锁10000字作文?有人说文学是一种记忆,此时我坐在电脑前,一边听着清脆的敲击声,一边回忆着你。你大我一岁,我小你一岁。我们一起长大,十指相扣,仿佛牢固的铜锁,紧紧锁着。那年夏天,漫长的一个多月里,妈妈每天背着我去山上的诊所治疗麻疹,你总是一同去。以下是张诗冬写的《锁》范文;
好锁作文10000字概况
- 作者:张诗冬
- 班级:高中高三
- 字数:10000字作文
- 体裁:
- 段落:分99段叙写
- 更新:2024年07月27日 10时22分
有人说文学是一种记忆,此时我坐在电脑前,一边听着清脆的敲击声,一边回忆着你。
你大我一岁,我小你一岁。我们一起长大,十指相扣,仿佛牢固的铜锁,紧紧锁着。
那年夏天,漫长的一个多月里,妈妈每天背着我去山上的诊所治疗麻疹,你总是一同去。回来时,我头上盖着毛巾无力地趴在妈妈的背上,你一手拉着妈妈的衣角,一手提着一袋雪白剔透的冰糖。我们都爱吃冰糖,脆脆的,甜甜的,洁白而透明。也就是那年,原本胖嘟嘟的我和你一般瘦了,开始了我们“双胞胎”的生活。那年你四岁,我三岁。
我和妈妈比较像,脸圆圆的,胖胖的;你和爸爸比较像,脸尖尖的,瘦瘦的。妈妈的头发是中分齐刘海,爸爸的头发三七分。妈妈总在为我们修正了可爱的学生头之后再剪出齐齐的刘海,可你总学着爸爸的样子将它们拂向一侧。
我们有时会玩这样的游戏:晚上一家人一起看电视时,你和爸妈一同坐在圆桌旁,我一个人坐在后边的沙发上。有时,他们会突然意识到“你”不见了,环顾四周,原来“你”在沙发上。哈哈,这时我们就会笑得很开心,因为他们往往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其实你是一直在他们旁边的,他们却错把我们认反了。因为我学着你的样子,将刘海扫向了一旁,你却将刘海梳了下来,这样一来不仔细看根本就分辨不出我们……那一年你七岁,我六岁。
放学回家的路上,偶遇一个卖小挂饰的小贩,简陋的木架上琳琅满目的叮叮当当的小东西吸引力很多小学生的目光,包括你我。好奇地凑上去,发现一对项链很漂亮,分别缀着闪闪的一把小锁和一个同样闪亮的小钥匙。心理很是喜欢,琢磨着要怎样杀价,但不论怎样,除非那小贩慈悲地将它们赠予我们,否则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用身上仅有的少得可怜的钱把它们收入囊中。无奈只得小心翼翼地,近乎讨好地询问她明天是否还会来到这儿,她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
我一直记恨那个女人,因为,翌日我们兴冲冲地带着足够的钱来到她前一日驻扎的地方时,她一直没有出现,中午没来,下午也没来!我慷慨地使用了当时记得的所有诅咒来表达我心中的不满甚至愤怒,我当时那么做着,并一直都那么做着。那一年你十一岁,我十岁。
我睡得很不安稳,醒来时朦胧中看见一片黑糊糊的影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我晚上流的鼻血。或许称得上悲壮,它覆盖了枕巾的一半面积,妈妈的背上也全是血。我的手指上满是血,是在睡梦中不安地擦着鼻子时沾染上的。十一个小时后,你最后一次出现,我被拖着,没有见到你,只是听说你从出现的那一刻起,鼻血便汩汩地流着,怎么都停不下来……
三毛习惯将荷西离开她的那一年称作“最后一年”。在你我的最后一年里我们的摩擦莫名地少了许多,我总和你黏在一块,生活的交集和并集是相等的,我的朋友几乎全是你的同学。她们大多住在一个院子里,我们经常跑到大院的后山上玩女孩都爱玩的扮家家。大家躺在干草和树枝铺成的“床”上,枕着金黄的落叶,假象夜幕已经降临,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了家中,开始睡觉了。秋风凉凉的,我轻轻地告诉你我觉得有点冷,你便脱了妈妈织的冒险外套给我盖上,很温暖的感觉。可是你原本穿得也不多,这么一来,你穿得就太单薄了。那一年你十二岁,我十一岁。
《挪威的森林》里渡边在不知不觉逝去的光阴里总是想起木月,想到自己的年龄不断地增长着,而木月却在另一个世界里,一直那么年轻着,永远都是十九岁。我如今已经长大,而你,却永远定格在那纯真的十二岁。
我们曾讨论过你升入中学后,该谁拿钥匙,放学后由谁来等着另一个一同回家。可这样的讨论在某一天突然失去了意义。当我一个人站在冰冷的铁门前,掏出那把钥匙开门时,偶尔会不自觉地怔住,以一种停止思维的方式呆滞地站着。
手中握着的钥匙渐渐有了温度,这钥匙原本应该是属于你的吧。锁还是之前的锁,没有更换,但是你没了钥匙,我们忘记给你捎上一把了,那么当你想进来时你该怎么办?你是不是不得不孤单地徘徊在门外,无声地乞求我们对你到来的感知?
正如梦中一般,妈妈打开门,看见一袭你默默地站在门外,提着一个黑色的小行李箱,她从看见你的那一刻起便又哭又骂,梦中的你是不辞而别的,似乎是去了哪儿旅游。你一直沉默着,只是那么站着。我恍惚觉得不认识你了,但又肯定那就是你。
而后的梦总是教会我现实,你在梦中和我一起玩,可我总隐约感觉有人说文学是一种记忆,此时我坐在电脑前,一边听着清脆的敲击声,一边回忆着你。你大我一岁,我小你一岁。我们一起长大,十指相扣,仿佛牢固的铜锁,紧紧锁着。
那年夏天,漫长的一个多月里,妈妈每天背着我去山上的诊所治疗麻疹,你总是一同去。回来时,我头上盖着毛巾无力地趴在妈妈的背上,你一手拉着妈妈的衣角,一手提着一袋雪白剔透的冰糖。我们都爱吃冰糖,脆脆的,甜甜的,洁白而透明。也就是那年,原本胖嘟嘟的我和你一般瘦了,开始了我们“双胞胎”的生活。那年你四岁,我三岁。
我和妈妈比较像,脸圆圆的,胖胖的;你和爸爸比较像,脸尖尖的,瘦瘦的。妈妈的头发是中分齐刘海,爸爸的头发三七分。妈妈总在为我们修正了可爱的学生头之后再剪出齐齐的刘海,可你总学着爸爸的样子将它们拂向一侧。
我们有时会玩这样的游戏:晚上一家人一起看电视时,你和爸妈一同坐在圆桌旁,我一个人坐在后边的沙发上。有时,他们会突然意识到“你”不见了,环顾四周,原来“你”在沙发上。哈哈,这时我们就会笑得很开心,因为他们往往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其实你是一直在他们旁边的,他们却错把我们认反了。因为我学着你的样子,将刘海扫向了一旁,你却将刘海梳了下来,这样一来不仔细看根本就分辨不出我们……那一年你七岁,我六岁。
放学回家的路上,偶遇一个卖小挂饰的小贩,简陋的木架上琳琅满目的叮叮当当的小东西吸引力很多小学生的目光,包括你我。好奇地凑上去,发现一对项链很漂亮,分别缀着闪闪的一把小锁和一个同样闪亮的小钥匙。心理很是喜欢,琢磨着要怎样杀价,但不论怎样,除非那小贩慈悲地将它们赠予我们,否则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用身上仅有的少得可怜的钱把它们收入囊中。无奈只得小心翼翼地,近乎讨好地询问她明天是否还会来到这儿,她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
我一直记恨那个女人,因为,翌日我们兴冲冲地带着足够的钱来到她前一日驻扎的地方时,她一直没有出现,中午没来,下午也没来!我慷慨地使用了当时记得的所有诅咒来表达我心中的不满甚至愤怒,我当时那么做着,并一直都那么做着。那一年你十一岁,我十岁。
我睡得很不安稳,醒来时朦胧中看见一片黑糊糊的影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我晚上流的鼻血。或许称得上悲壮,它覆盖了枕巾的一半面积,妈妈的背上也全是血。我的手指上满是血,是在睡梦中不安地擦着鼻子时沾染上的。十一个小时后,你最后一次出现,我被拖着,没有见到你,只是听说你从出现的那一刻起,鼻血便汩汩地流着,怎么都停不下来……
三毛习惯将荷西离开她的那一年称作“最后一年”。在你我的最后一年里我们的摩擦莫名地少了许多,我总和你黏在一块,生活的交集和并集是相等的,我的朋友几乎全是你的同学。她们大多住在一个院子里,我们经常跑到大院的后山上玩女孩都爱玩的扮家家。大家躺在干草和树枝铺成的“床”上,枕着金黄的落叶,假象夜幕已经降临,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了家中,开始睡觉了。秋风凉凉的,我轻轻地告诉你我觉得有点冷,你便脱了妈妈织的冒险外套给我盖上,很温暖的感觉。可是你原本穿得也不多,这么一来,你穿得就太单薄了。那一年你十二岁,我十一岁。
《挪威的森林》里渡边在不知不觉逝去的光阴里总是想起木月,想到自己的年龄不断地增长着,而木月却在另一个世界里,一直那么年轻着,永远都是十九岁。我如今已经长大,而你,却永远定格在那纯真的十二岁。
我们曾讨论过你升入中学后,该谁拿钥匙,放学后由谁来等着另一个一同回家。可这样的讨论在某一天突然失去了意义。当我一个人站在冰冷的铁门前,掏出那把钥匙开门时,偶尔会不自觉地怔住,以一种停止思维的方式呆滞地站着。
手中握着的钥匙渐渐有了温度,这钥匙原本应该是属于你的吧。锁还是之前的锁,没有更换,但是你没了钥匙,我们忘记给你捎上一把了,那么当你想进来时你该怎么办?你是不是不得不孤单地徘徊在门外,无声地乞求我们对你到来的感知?
正如梦中一般,妈妈打开门,看见一袭你默默地站在门外,提着一个黑色的小行李箱,她从看见你的那一刻起便又哭又骂,梦中的你是不辞而别的,似乎是去了哪儿旅游。你一直沉默着,只是那么站着。我恍惚觉得不认识你了,但又肯定那就是你。
而后的梦总是教会我现实,你在梦中和我一起玩,可我总隐约感觉有人说文学是一种记忆,此时我坐在电脑前,一边听着清脆的敲击声,一边回忆着你。你大我一岁,我小你一岁。我们一起长大,十指相扣,仿佛牢固的铜锁,紧紧锁着。
那年夏天,漫长的一个多月里,妈妈每天背着我去山上的诊所治疗麻疹,你总是一同去。回来时,我头上盖着毛巾无力地趴在妈妈的背上,你一手拉着妈妈的衣角,一手提着一袋雪白剔透的冰糖。我们都爱吃冰糖,脆脆的,甜甜的,洁白而透明。也就是那年,原本胖嘟嘟的我和你一般瘦了,开始了我们“双胞胎”的生活。那年你四岁,我三岁。
我和妈妈比较像,脸圆圆的,胖胖的;你和爸爸比较像,脸尖尖的,瘦瘦的。妈妈的头发是中分齐刘海,爸爸的头发三七分。妈妈总在为我们修正了可爱的学生头之后再剪出齐齐的刘海,可你总学着爸爸的样子将它们拂向一侧。
我们有时会玩这样的游戏:晚上一家人一起看电视时,你和爸妈一同坐在圆桌旁,我一个人坐在后边的沙发上。有时,他们会突然意识到“你”不见了,环顾四周,原来“你”在沙发上。哈哈,这时我们就会笑得很开心,因为他们往往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其实你是一直在他们旁边的,他们却错把我们认反了。因为我学着你的样子,将刘海扫向了一旁,你却将刘海梳了下来,这样一来不仔细看根本就分辨不出我们……那一年你七岁,我六岁。
放学回家的路上,偶遇一个卖小挂饰的小贩,简陋的木架上琳琅满目的叮叮当当的小东西吸引力很多小学生的目光,包括你我。好奇地凑上去,发现一对项链很漂亮,分别缀着闪闪的一把小锁和一个同样闪亮的小钥匙。心理很是喜欢,琢磨着要怎样杀价,但不论怎样,除非那小贩慈悲地将它们赠予我们,否则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用身上仅有的少得可怜的钱把它们收入囊中。无奈只得小心翼翼地,近乎讨好地询问她明天是否还会来到这儿,她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
我一直记恨那个女人,因为,翌日我们兴冲冲地带着足够的钱来到她前一日驻扎的地方时,她一直没有出现,中午没来,下午也没来!我慷慨地使用了当时记得的所有诅咒来表达我心中的不满甚至愤怒,我当时那么做着,并一直都那么做着。那一年你十一岁,我十岁。
我睡得很不安稳,醒来时朦胧中看见一片黑糊糊的影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我晚上流的鼻血。或许称得上悲壮,它覆盖了枕巾的一半面积,妈妈的背上也全是血。我的手指上满是血,是在睡梦中不安地擦着鼻子时沾染上的。十一个小时后,你最后一次出现,我被拖着,没有见到你,只是听说你从出现的那一刻起,鼻血便汩汩地流着,怎么都停不下来……
三毛习惯将荷西离开她的那一年称作“最后一年”。在你我的最后一年里我们的摩擦莫名地少了许多,我总和你黏在一块,生活的交集和并集是相等的,我的朋友几乎全是你的同学。她们大多住在一个院子里,我们经常跑到大院的后山上玩女孩都爱玩的扮家家。大家躺在干草和树枝铺成的“床”上,枕着金黄的落叶,假象夜幕已经降临,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了家中,开始睡觉了。秋风凉凉的,我轻轻地告诉你我觉得有点冷,你便脱了妈妈织的冒险外套给我盖上,很温暖的感觉。可是你原本穿得也不多,这么一来,你穿得就太单薄了。那一年你十二岁,我十一岁。
《挪威的森林》里渡边在不知不觉逝去的光阴里总是想起木月,想到自己的年龄不断地增长着,而木月却在另一个世界里,一直那么年轻着,永远都是十九岁。我如今已经长大,而你,却永远定格在那纯真的十二岁。
我们曾讨论过你升入中学后,该谁拿钥匙,放学后由谁来等着另一个一同回家。可这样的讨论在某一天突然失去了意义。当我一个人站在冰冷的铁门前,掏出那把钥匙开门时,偶尔会不自觉地怔住,以一种停止思维的方式呆滞地站着。
手中握着的钥匙渐渐有了温度,这钥匙原本应该是属于你的吧。锁还是之前的锁,没有更换,但是你没了钥匙,我们忘记给你捎上一把了,那么当你想进来时你该怎么办?你是不是不得不孤单地徘徊在门外,无声地乞求我们对你到来的感知?
正如梦中一般,妈妈打开门,看见一袭你默默地站在门外,提着一个黑色的小行李箱,她从看见你的那一刻起便又哭又骂,梦中的你是不辞而别的,似乎是去了哪儿旅游。你一直沉默着,只是那么站着。我恍惚觉得不认识你了,但又肯定那就是你。
而后的梦总是教会我现实,你在梦中和我一起玩,可我总隐约感觉有人说文学是一种记忆,此时我坐在电脑前,一边听着清脆的敲击声,一边回忆着你。你大我一岁,我小你一岁。我们一起长大,十指相扣,仿佛牢固的铜锁,紧紧锁着。
那年夏天,漫长的一个多月里,妈妈每天背着我去山上的诊所治疗麻疹,你总是一同去。回来时,我头上盖着毛巾无力地趴在妈妈的背上,你一手拉着妈妈的衣角,一手提着一袋雪白剔透的冰糖。我们都爱吃冰糖,脆脆的,甜甜的,洁白而透明。也就是那年,原本胖嘟嘟的我和你一般瘦了,开始了我们“双胞胎”的生活。那年你四岁,我三岁。
我和妈妈比较像,脸圆圆的,胖胖的;你和爸爸比较像,脸尖尖的,瘦瘦的。妈妈的头发是中分齐刘海,爸爸的头发三七分。妈妈总在为我们修正了可爱的学生头之后再剪出齐齐的刘海,可你总学着爸爸的样子将它们拂向一侧。
我们有时会玩这样的游戏:晚上一家人一起看电视时,你和爸妈一同坐在圆桌旁,我一个人坐在后边的沙发上。有时,他们会突然意识到“你”不见了,环顾四周,原来“你”在沙发上。哈哈,这时我们就会笑得很开心,因为他们往往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其实你是一直在他们旁边的,他们却错把我们认反了。因为我学着你的样子,将刘海扫向了一旁,你却将刘海梳了下来,这样一来不仔细看根本就分辨不出我们……那一年你七岁,我六岁。
放学回家的路上,偶遇一个卖小挂饰的小贩,简陋的木架上琳琅满目的叮叮当当的小东西吸引力很多小学生的目光,包括你我。好奇地凑上去,发现一对项链很漂亮,分别缀着闪闪的一把小锁和一个同样闪亮的小钥匙。心理很是喜欢,琢磨着要怎样杀价,但不论怎样,除非那小贩慈悲地将它们赠予我们,否则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用身上仅有的少得可怜的钱把它们收入囊中。无奈只得小心翼翼地,近乎讨好地询问她明天是否还会来到这儿,她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
我一直记恨那个女人,因为,翌日我们兴冲冲地带着足够的钱来到她前一日驻扎的地方时,她一直没有出现,中午没来,下午也没来!我慷慨地使用了当时记得的所有诅咒来表达我心中的不满甚至愤怒,我当时那么做着,并一直都那么做着。那一年你十一岁,我十岁。
我睡得很不安稳,醒来时朦胧中看见一片黑糊糊的影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我晚上流的鼻血。或许称得上悲壮,它覆盖了枕巾的一半面积,妈妈的背上也全是血。我的手指上满是血,是在睡梦中不安地擦着鼻子时沾染上的。十一个小时后,你最后一次出现,我被拖着,没有见到你,只是听说你从出现的那一刻起,鼻血便汩汩地流着,怎么都停不下来……
三毛习惯将荷西离开她的那一年称作“最后一年”。在你我的最后一年里我们的摩擦莫名地少了许多,我总和你黏在一块,生活的交集和并集是相等的,我的朋友几乎全是你的同学。她们大多住在一个院子里,我们经常跑到大院的后山上玩女孩都爱玩的扮家家。大家躺在干草和树枝铺成的“床”上,枕着金黄的落叶,假象夜幕已经降临,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了家中,开始睡觉了。秋风凉凉的,我轻轻地告诉你我觉得有点冷,你便脱了妈妈织的冒险外套给我盖上,很温暖的感觉。可是你原本穿得也不多,这么一来,你穿得就太单薄了。那一年你十二岁,我十一岁。
《挪威的森林》里渡边在不知不觉逝去的光阴里总是想起木月,想到自己的年龄不断地增长着,而木月却在另一个世界里,一直那么年轻着,永远都是十九岁。我如今已经长大,而你,却永远定格在那纯真的十二岁。
我们曾讨论过你升入中学后,该谁拿钥匙,放学后由谁来等着另一个一同回家。可这样的讨论在某一天突然失去了意义。当我一个人站在冰冷的铁门前,掏出那把钥匙开门时,偶尔会不自觉地怔住,以一种停止思维的方式呆滞地站着。
手中握着的钥匙渐渐有了温度,这钥匙原本应该是属于你的吧。锁还是之前的锁,没有更换,但是你没了钥匙,我们忘记给你捎上一把了,那么当你想进来时你该怎么办?你是不是不得不孤单地徘徊在门外,无声地乞求我们对你到来的感知?
正如梦中一般,妈妈打开门,看见一袭你默默地站在门外,提着一个黑色的小行李箱,她从看见你的那一刻起便又哭又骂,梦中的你是不辞而别的,似乎是去了哪儿旅游。你一直沉默着,只是那么站着。我恍惚觉得不认识你了,但又肯定那就是你。
而后的梦总是教会我现实,你在梦中和我一起玩,可我总隐约感觉有人说文学是一种记忆,此时我坐在电脑前,一边听着清脆的敲击声,一边回忆着你。你大我一岁,我小你一岁。我们一起长大,十指相扣,仿佛牢固的铜锁,紧紧锁着。
那年夏天,漫长的一个多月里,妈妈每天背着我去山上的诊所治疗麻疹,你总是一同去。回来时,我头上盖着毛巾无力地趴在妈妈的背上,你一手拉着妈妈的衣角,一手提着一袋雪白剔透的冰糖。我们都爱吃冰糖,脆脆的,甜甜的,洁白而透明。也就是那年,原本胖嘟嘟的我和你一般瘦了,开始了我们“双胞胎”的生活。那年你四岁,我三岁。
我和妈妈比较像,脸圆圆的,胖胖的;你和爸爸比较像,脸尖尖的,瘦瘦的。妈妈的头发是中分齐刘海,爸爸的头发三七分。妈妈总在为我们修正了可爱的学生头之后再剪出齐齐的刘海,可你总学着爸爸的样子将它们拂向一侧。
我们有时会玩这样的游戏:晚上一家人一起看电视时,你和爸妈一同坐在圆桌旁,我一个人坐在后边的沙发上。有时,他们会突然意识到“你”不见了,环顾四周,原来“你”在沙发上。哈哈,这时我们就会笑得很开心,因为他们往往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其实你是一直在他们旁边的,他们却错把我们认反了。因为我学着你的样子,将刘海扫向了一旁,你却将刘海梳了下来,这样一来不仔细看根本就分辨不出我们……那一年你七岁,我六岁。
放学回家的路上,偶遇一个卖小挂饰的小贩,简陋的木架上琳琅满目的叮叮当当的小东西吸引力很多小学生的目光,包括你我。好奇地凑上去,发现一对项链很漂亮,分别缀着闪闪的一把小锁和一个同样闪亮的小钥匙。心理很是喜欢,琢磨着要怎样杀价,但不论怎样,除非那小贩慈悲地将它们赠予我们,否则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用身上仅有的少得可怜的钱把它们收入囊中。无奈只得小心翼翼地,近乎讨好地询问她明天是否还会来到这儿,她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
我一直记恨那个女人,因为,翌日我们兴冲冲地带着足够的钱来到她前一日驻扎的地方时,她一直没有出现,中午没来,下午也没来!我慷慨地使用了当时记得的所有诅咒来表达我心中的不满甚至愤怒,我当时那么做着,并一直都那么做着。那一年你十一岁,我十岁。
我睡得很不安稳,醒来时朦胧中看见一片黑糊糊的影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我晚上流的鼻血。或许称得上悲壮,它覆盖了枕巾的一半面积,妈妈的背上也全是血。我的手指上满是血,是在睡梦中不安地擦着鼻子时沾染上的。十一个小时后,你最后一次出现,我被拖着,没有见到你,只是听说你从出现的那一刻起,鼻血便汩汩地流着,怎么都停不下来……
三毛习惯将荷西离开她的那一年称作“最后一年”。在你我的最后一年里我们的摩擦莫名地少了许多,我总和你黏在一块,生活的交集和并集是相等的,我的朋友几乎全是你的同学。她们大多住在一个院子里,我们经常跑到大院的后山上玩女孩都爱玩的扮家家。大家躺在干草和树枝铺成的“床”上,枕着金黄的落叶,假象夜幕已经降临,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了家中,开始睡觉了。秋风凉凉的,我轻轻地告诉你我觉得有点冷,你便脱了妈妈织的冒险外套给我盖上,很温暖的感觉。可是你原本穿得也不多,这么一来,你穿得就太单薄了。那一年你十二岁,我十一岁。
《挪威的森林》里渡边在不知不觉逝去的光阴里总是想起木月,想到自己的年龄不断地增长着,而木月却在另一个世界里,一直那么年轻着,永远都是十九岁。我如今已经长大,而你,却永远定格在那纯真的十二岁。
我们曾讨论过你升入中学后,该谁拿钥匙,放学后由谁来等着另一个一同回家。可这样的讨论在某一天突然失去了意义。当我一个人站在冰冷的铁门前,掏出那把钥匙开门时,偶尔会不自觉地怔住,以一种停止思维的方式呆滞地站着。
手中握着的钥匙渐渐有了温度,这钥匙原本应该是属于你的吧。锁还是之前的锁,没有更换,但是你没了钥匙,我们忘记给你捎上一把了,那么当你想进来时你该怎么办?你是不是不得不孤单地徘徊在门外,无声地乞求我们对你到来的感知?
正如梦中一般,妈妈打开门,看见一袭你默默地站在门外,提着一个黑色的小行李箱,她从看见你的那一刻起便又哭又骂,梦中的你是不辞而别的,似乎是去了哪儿旅游。你一直沉默着,只是那么站着。我恍惚觉得不认识你了,但又肯定那就是你。
而后的梦总是教会我现实,你在梦中和我一起玩,可我总隐约感觉有人说文学是一种记忆,此时我坐在电脑前,一边听着清脆的敲击声,一边回忆着你。你大我一岁,我小你一岁。我们一起长大,十指相扣,仿佛牢固的铜锁,紧紧锁着。
那年夏天,漫长的一个多月里,妈妈每天背着我去山上的诊所治疗麻疹,你总是一同去。回来时,我头上盖着毛巾无力地趴在妈妈的背上,你一手拉着妈妈的衣角,一手提着一袋雪白剔透的冰糖。我们都爱吃冰糖,脆脆的,甜甜的,洁白而透明。也就是那年,原本胖嘟嘟的我和你一般瘦了,开始了我们“双胞胎”的生活。那年你四岁,我三岁。
我和妈妈比较像,脸圆圆的,胖胖的;你和爸爸比较像,脸尖尖的,瘦瘦的。妈妈的头发是中分齐刘海,爸爸的头发三七分。妈妈总在为我们修正了可爱的学生头之后再剪出齐齐的刘海,可你总学着爸爸的样子将它们拂向一侧。
我们有时会玩这样的游戏:晚上一家人一起看电视时,你和爸妈一同坐在圆桌旁,我一个人坐在后边的沙发上。有时,他们会突然意识到“你”不见了,环顾四周,原来“你”在沙发上。哈哈,这时我们就会笑得很开心,因为他们往往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其实你是一直在他们旁边的,他们却错把我们认反了。因为我学着你的样子,将刘海扫向了一旁,你却将刘海梳了下来,这样一来不仔细看根本就分辨不出我们……那一年你七岁,我六岁。
放学回家的路上,偶遇一个卖小挂饰的小贩,简陋的木架上琳琅满目的叮叮当当的小东西吸引力很多小学生的目光,包括你我。好奇地凑上去,发现一对项链很漂亮,分别缀着闪闪的一把小锁和一个同样闪亮的小钥匙。心理很是喜欢,琢磨着要怎样杀价,但不论怎样,除非那小贩慈悲地将它们赠予我们,否则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用身上仅有的少得可怜的钱把它们收入囊中。无奈只得小心翼翼地,近乎讨好地询问她明天是否还会来到这儿,她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
我一直记恨那个女人,因为,翌日我们兴冲冲地带着足够的钱来到她前一日驻扎的地方时,她一直没有出现,中午没来,下午也没来!我慷慨地使用了当时记得的所有诅咒来表达我心中的不满甚至愤怒,我当时那么做着,并一直都那么做着。那一年你十一岁,我十岁。
我睡得很不安稳,醒来时朦胧中看见一片黑糊糊的影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我晚上流的鼻血。或许称得上悲壮,它覆盖了枕巾的一半面积,妈妈的背上也全是血。我的手指上满是血,是在睡梦中不安地擦着鼻子时沾染上的。十一个小时后,你最后一次出现,我被拖着,没有见到你,只是听说你从出现的那一刻起,鼻血便汩汩地流着,怎么都停不下来……
三毛习惯将荷西离开她的那一年称作“最后一年”。在你我的最后一年里我们的摩擦莫名地少了许多,我总和你黏在一块,生活的交集和并集是相等的,我的朋友几乎全是你的同学。她们大多住在一个院子里,我们经常跑到大院的后山上玩女孩都爱玩的扮家家。大家躺在干草和树枝铺成的“床”上,枕着金黄的落叶,假象夜幕已经降临,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了家中,开始睡觉了。秋风凉凉的,我轻轻地告诉你我觉得有点冷,你便脱了妈妈织的冒险外套给我盖上,很温暖的感觉。可是你原本穿得也不多,这么一来,你穿得就太单薄了。那一年你十二岁,我十一岁。
《挪威的森林》里渡边在不知不觉逝去的光阴里总是想起木月,想到自己的年龄不断地增长着,而木月却在另一个世界里,一直那么年轻着,永远都是十九岁。我如今已经长大,而你,却永远定格在那纯真的十二岁。
我们曾讨论过你升入中学后,该谁拿钥匙,放学后由谁来等着另一个一同回家。可这样的讨论在某一天突然失去了意义。当我一个人站在冰冷的铁门前,掏出那把钥匙开门时,偶尔会不自觉地怔住,以一种停止思维的方式呆滞地站着。
手中握着的钥匙渐渐有了温度,这钥匙原本应该是属于你的吧。锁还是之前的锁,没有更换,但是你没了钥匙,我们忘记给你捎上一把了,那么当你想进来时你该怎么办?你是不是不得不孤单地徘徊在门外,无声地乞求我们对你到来的感知?
正如梦中一般,妈妈打开门,看见一袭你默默地站在门外,提着一个黑色的小行李箱,她从看见你的那一刻起便又哭又骂,梦中的你是不辞而别的,似乎是去了哪儿旅游。你一直沉默着,只是那么站着。我恍惚觉得不认识你了,但又肯定那就是你。
而后的梦总是教会我现实,你在梦中和我一起玩,可我总隐约感觉有人说文学是一种记忆,此时我坐在电脑前,一边听着清脆的敲击声,一边回忆着你。你大我一岁,我小你一岁。我们一起长大,十指相扣,仿佛牢固的铜锁,紧紧锁着。
那年夏天,漫长的一个多月里,妈妈每天背着我去山上的诊所治疗麻疹,你总是一同去。回来时,我头上盖着毛巾无力地趴在妈妈的背上,你一手拉着妈妈的衣角,一手提着一袋雪白剔透的冰糖。我们都爱吃冰糖,脆脆的,甜甜的,洁白而透明。也就是那年,原本胖嘟嘟的我和你一般瘦了,开始了我们“双胞胎”的生活。那年你四岁,我三岁。
我和妈妈比较像,脸圆圆的,胖胖的;你和爸爸比较像,脸尖尖的,瘦瘦的。妈妈的头发是中分齐刘海,爸爸的头发三七分。妈妈总在为我们修正了可爱的学生头之后再剪出齐齐的刘海,可你总学着爸爸的样子将它们拂向一侧。
我们有时会玩这样的游戏:晚上一家人一起看电视时,你和爸妈一同坐在圆桌旁,我一个人坐在后边的沙发上。有时,他们会突然意识到“你”不见了,环顾四周,原来“你”在沙发上。哈哈,这时我们就会笑得很开心,因为他们往往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其实你是一直在他们旁边的,他们却错把我们认反了。因为我学着你的样子,将刘海扫向了一旁,你却将刘海梳了下来,这样一来不仔细看根本就分辨不出我们……那一年你七岁,我六岁。
放学回家的路上,偶遇一个卖小挂饰的小贩,简陋的木架上琳琅满目的叮叮当当的小东西吸引力很多小学生的目光,包括你我。好奇地凑上去,发现一对项链很漂亮,分别缀着闪闪的一把小锁和一个同样闪亮的小钥匙。心理很是喜欢,琢磨着要怎样杀价,但不论怎样,除非那小贩慈悲地将它们赠予我们,否则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用身上仅有的少得可怜的钱把它们收入囊中。无奈只得小心翼翼地,近乎讨好地询问她明天是否还会来到这儿,她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
我一直记恨那个女人,因为,翌日我们兴冲冲地带着足够的钱来到她前一日驻扎的地方时,她一直没有出现,中午没来,下午也没来!我慷慨地使用了当时记得的所有诅咒来表达我心中的不满甚至愤怒,我当时那么做着,并一直都那么做着。那一年你十一岁,我十岁。
我睡得很不安稳,醒来时朦胧中看见一片黑糊糊的影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我晚上流的鼻血。或许称得上悲壮,它覆盖了枕巾的一半面积,妈妈的背上也全是血。我的手指上满是血,是在睡梦中不安地擦着鼻子时沾染上的。十一个小时后,你最后一次出现,我被拖着,没有见到你,只是听说你从出现的那一刻起,鼻血便汩汩地流着,怎么都停不下来……
三毛习惯将荷西离开她的那一年称作“最后一年”。在你我的最后一年里我们的摩擦莫名地少了许多,我总和你黏在一块,生活的交集和并集是相等的,我的朋友几乎全是你的同学。她们大多住在一个院子里,我们经常跑到大院的后山上玩女孩都爱玩的扮家家。大家躺在干草和树枝铺成的“床”上,枕着金黄的落叶,假象夜幕已经降临,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了家中,开始睡觉了。秋风凉凉的,我轻轻地告诉你我觉得有点冷,你便脱了妈妈织的冒险外套给我盖上,很温暖的感觉。可是你原本穿得也不多,这么一来,你穿得就太单薄了。那一年你十二岁,我十一岁。
《挪威的森林》里渡边在不知不觉逝去的光阴里总是想起木月,想到自己的年龄不断地增长着,而木月却在另一个世界里,一直那么年轻着,永远都是十九岁。我如今已经长大,而你,却永远定格在那纯真的十二岁。
我们曾讨论过你升入中学后,该谁拿钥匙,放学后由谁来等着另一个一同回家。可这样的讨论在某一天突然失去了意义。当我一个人站在冰冷的铁门前,掏出那把钥匙开门时,偶尔会不自觉地怔住,以一种停止思维的方式呆滞地站着。
手中握着的钥匙渐渐有了温度,这钥匙原本应该是属于你的吧。锁还是之前的锁,没有更换,但是你没了钥匙,我们忘记给你捎上一把了,那么当你想进来时你该怎么办?你是不是不得不孤单地徘徊在门外,无声地乞求我们对你到来的感知?
正如梦中一般,妈妈打开门,看见一袭你默默地站在门外,提着一个黑色的小行李箱,她从看见你的那一刻起便又哭又骂,梦中的你是不辞而别的,似乎是去了哪儿旅游。你一直沉默着,只是那么站着。我恍惚觉得不认识你了,但又肯定那就是你。
而后的梦总是教会我现实,你在梦中和我一起玩,可我总隐约感觉

好文章,赞一下
585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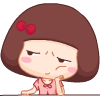
很一般,需努力
1685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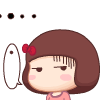
太差劲,踩一下
74人
- 上一篇:离别·友谊·接受·努力作文1000字
- 下一篇:她真的蠢吗?作文550字